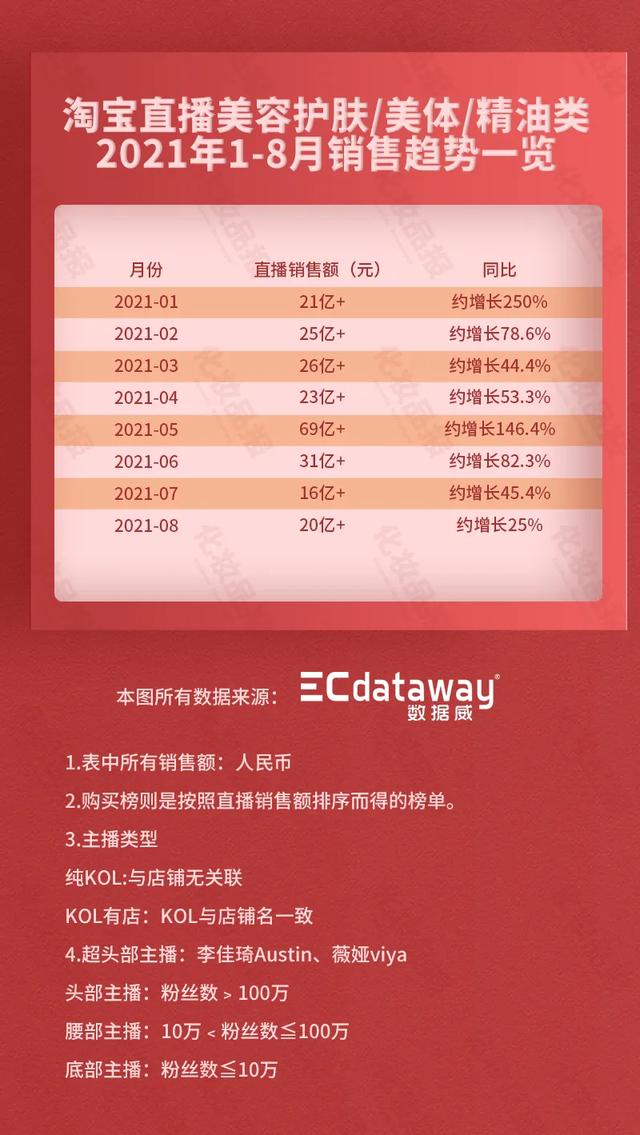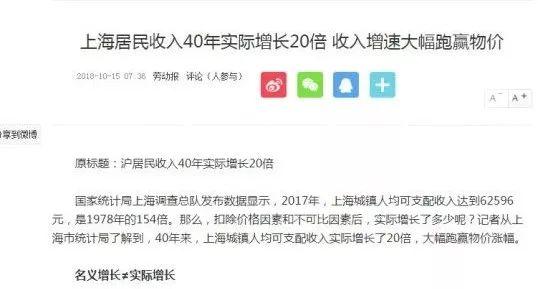12月3日下午,上海奉贤法院召开《2020-2021年上半年东方美姑商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白皮书指出,随着流媒体技术的成熟,许多企业不仅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推出产品,还通过互联网网站、应用软件和微信小程序等,以视频直播、音频直播、图文直播或多种直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产品营销。由此产生的商业冲突和纠纷在近两年变得突出。上海奉贤法院审理了一起网络直播带货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0年11月,奉贤东方美谷某商业公司(甲方)与某文化传媒公司(乙方)签订直播服务合作协议,约定文化传媒公司负责安排主播在Tik Tok直播平台为该商业公司产品提供直播服务,推广费25万元。根据协议,25万元推广费对应的保底销售额为250万元。如果乙方现场促销产生的实际销售额(不包括退换货)未达到本条约定的保证销售额,乙方应按比例向甲方退还乙方已收取的促销费。此外,协议还约定,乙方及乙方主播不得向甲方支付相当于退货单涉案金额30%的违约金,不得在下单后恶意退货或虚假增加甲方店铺销售额。但事后,商业公司认为文化传媒公司下单后存在刷单、恶意退货等虚增销售行为,故起诉至法院,要求文化传媒公司退还多付的推广费。原告商业公司诉称,原告于2020年11月16日与被告签订直播服务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于2020年11月16日安排Tik Tok主播小李(化名)在Tik Tok直播平台直播销售原告产品。协议还约定,被告应在直播中完成250万元的保底销售额,原告已按约定支付推广费。后因被告未完成保底销售,且原告发现被告在直播当天存在恶意刷单行为,直播结束后次日至次日出现数千笔异常订单,退货退款率达85%,致使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被告的行为明显属于违约行为。在与被告确认真相后,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最迟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补种,但被告并未采取任何补种行动,且拒绝退还推广费。多次协商未果后,原告提起诉讼。被告文化传媒公司辩称,虽然双方签订了直播服务合作协议,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推广费25万元,但双方属于中介合同关系。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被告帮助原告与主播小李达成直播销售的协议,并从中获取中介服务费,被告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被告也认为不需要退还推广费,退货的原因可能是原告提供的产品质量不符合标准。法院:被告存在刷单行为。法院认为,被告存在刷单、下单后恶意退货等虚增销售行为。首先,根据原告提交的Tik Tok店后台数据,在近五个小时的短暂直播时间内,退款率高达85.25%,人均退货2.02件,明显不正常。其次,在直播结束以及直播结束后的第二天,原告工作人员告知被告工作人员,被告主播刷单了。被告工作人员从未否认,但在没有复播希望的情况下,同意退还22万余元。
再次,被告辩称退款率高是因为原告商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冲动消费。法院认为,在直播过程中,消费者一直没有收到商品,甚至商品还没有送达,不可能知道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但在直播过程中,消费者冲动消费、毁约、退单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毕竟是少数情况,不可能出现退款率超过85%的情况。然而,经法院审查,Tik Tok后台统计的销售数据并不是按照秒杀价格计算,而是按照商品的原价计算。因此,即使销量不准确,按照系统设定的原价计算的销售额也只能支持原告30%退款的请求。法官:花式开票更隐蔽。近年来,直播经济和网络名人经济蓬勃发展。企业在直播平台签订的一系列协议,通常都是直播平台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中包含大量“不时修订的交易规则和政策”。当存在直播平台无证经营、直播内容虚构、直播素材侵权、直播数据失真等情形时,企业往往因为接受并确认了上述格式协议而陷入无权主张产品损失的困境。上海市奉贤法院商事庭法官姚认为,从纠纷发生到诉讼形成,很多直播数据可能已经消失,这也是审理涉及直播纠纷的一大难点。“谁会保留这些数据?现在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官介绍,各方提供的数据,包括不同平台机构、直播间、运营商的数据,以及一些代理机构、中介机构的数据,都可能导致数据冲突和打架,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些销售数据也会影响商家最终的分成比例和佣金提取比例。比如构成实质性的开票行为,就要适当从销量中扣除。现在的花式刷单行为也具有隐蔽性,很难区分刷单导致的退货和消费者冲动或产品质量导致的退货纠纷。“所以在一开始约定服务合同的时候,商家和直播的营销平台机构之间,最好能提前就数据最终引用到哪里有个约定,这样可以避免后续的纠纷。”
来源|深思APP记者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