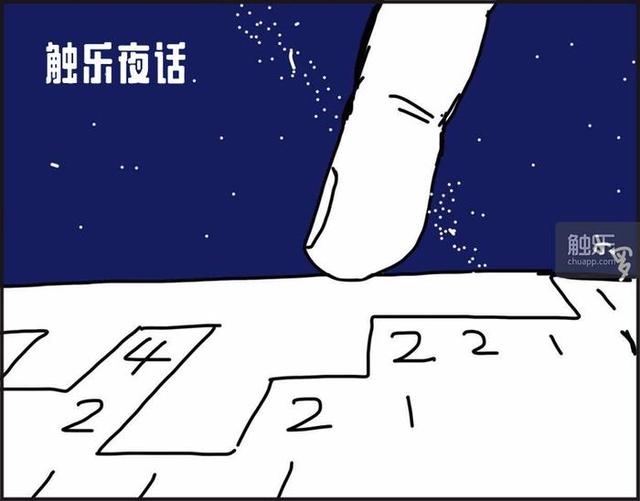
文中提到的一些人出现在《中国扫雷》一文中。这一次,我们应该继续谈论扫雷问题。它不是附录或后记。
我很想谈谈我的一个朋友。以前我的“扫雷”知识都是从她那里来的。
第一次见她是在饭桌上,十几个人坐在一起。我们彼此并不熟悉,彼此相视无言。在这样的用餐场合,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说起了“恋尸癖”。坐在我正对面,已经3岁16岁的她瞬间在头上竖起了隐藏的天线。
“啊,这就是波!这货和我是一类人!”——以上是设计线。

我们不在一个城市,然后不知怎么的,就在QQ上勾搭上了。
我们的同步率很惊人,而且不仅仅是口味相似——平时她在听某张唱片,我肯定正好在里面哼某首歌。以这种神秘的形式,我们在脑子里隔三差五空唱着《治安官黑猫》——直到我突然在电话里“向你致敬”乘以三,然后突然唱了出来,她才意识到,啊,又是这盏灯。
这种奇妙的电波,连儿歌都能比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碰壁”游戏。
那时候除了扫雷,她从来不玩游戏。按照国内扫雷圈的定义,就是所谓的“野玩家”。
其实扫雷舰玩家是非常容易暴露的。看到身边有人,没事就把分辨率调到“640x480”,故意放慢鼠标指针的移动速度,甚至放下椅子,只为调整一个合适的“坐高”,然后耳边响起一声短促的鼠标“咔嚓”声。毫无疑问,是她,是她。
那时候,她还在上大学。和我采访的世界女子扫雷冠军一样,她每天花7个多小时在宿舍里扫雷。她的室友也没说什么,只是不让她晚上玩——鼠标点得太勤,很吵。她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直到手疼脖子疼她才放弃,最后打了腱鞘炎。但她还是乐在其中。
当时我完全懵了。这样的跳棋游戏哪里好玩?——虽然作为一个数独爱好者,这样说似乎太丢人了。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问过她任何关于扫雷的问题。我不知道她上瘾的原因,也不知道她实际上是怎么玩的。虽然我们在电影、音乐等领域有着无数的共同点,但对于游戏,我们总是保持沉默。
——直到我做了扫雷的题目。
与周丹交谈后,我非常兴奋。讲的是看到一个“强而不自知”的高手的兴奋。如果拿歌手领域来类比,其他扫雷舰更倾向于“技术”,更像林志炫,沉迷于技术研究,无事可做,只把自己关在“录音棚”里反复锤炼。周丹很棒。她说她只会扫,对理论一窍不通,不知道怎么教自己的套路。她是凭本能在玩——当然,玩多了,肯定会形成条件反射。但能够玩出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还是任性的把她定义为“乐感流”,和王菲刚出道的时候差不多。
当时,我闻到了扫雷圈的这股风——因为周丹,扫雷的新世界大门向我打开了一条缝。能感觉到门板的厚度,能感觉到门槛的高度,能睁开眼睛看风景,但终究不知道怎么玩。我过不去那个门槛,也推不动门。我只能把空罐头气做的跟昨天一样,让你也闻闻。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清新气息?
有了这种能量,我跟我朋友说话就像面试一样,无非是好奇。作为一个野玩家,她是怎么入坑的,怎么看游戏,怎么玩,为什么喜欢玩?虽然我同意,喜欢就是喜欢,没有那么多理由。但突然之间,我想问明白。
然后才知道她是高级玩家,通关时间一般是90-120秒,最高纪录可以逼近60秒。在扫雷圈,一个野玩家可以跨越“人间界”的门槛100秒,甚至可以扫出“60秒”,已经接近“神界”,在雷友看来已经很强了。后来我看到郭,我一提这个,他马上跟我说:“拉进去,拉进去!”
我后来转达给她了。也是在这个时候,她说自己点开了扫雷网,看了大神的视频,甚至练过盲扫。但她没有上网,尽管她本可以推开门。
我记得最后一次问她为什么喜欢扫雷。她说她喜欢计算的过程,就像头脑风暴一样,像做数学题一样上瘾——虽然在我的记忆里,她数学不是很好。
厌倦了问她的问题,她只是说,她只是很享受那种“把自己空清零,只专注当下”的感觉。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到,她在痴迷扫雷之前所经历的,和“生命的暴击”差不多,那种负面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那段时间她一直在扫矿,扫了一遍又一遍,好像脱离了时间线。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想起最近看的《七帕说》。那一期的辩论题目是,“对于生活的暴击,我们应该感恩还是不感恩?”。那一期的嘉宾是我最喜欢的春夏,她选择了“不感恩”的立场。她在节目里说了下面一段话,我也有同感。
我想我也不感激生命的暴击——最感激的是我在暴击面前努力过。
她说,当时之所以不选择上网,是因为不追求速度,只享受过程。扫雷期间,她真的觉得很稳定,很幸福。我突然明白了她对扫雷的热爱。虽然这个原因可能和扫雷网的那些矿友不太一样。
昨晚,看完我的文章,她很激动。她电话告诉我,她想再玩一次扫雷,可惜Mac上没有。现在她18岁,8岁。我能感觉到她长大了。
最近我们在一起思考。哦,不对,《唱》这首歌是,“感受风的温差,感受世间的无常。”
写到这里才意识到,啊,这篇文章的图呢!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晒出我的猫——毕竟我的人生理想之一就是当我写出一篇真正牛逼的文章时,我能巧妙地让我的猫出现在以后每篇文章的某个地方,就像这样:
“他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体格,配备了‘即插即用’。他前后已经换过一次鼠标和鼠标垫四次,无缝对接,就像一只不用费心换食物的猫。”
不开玩笑,这是困扰我半个月,让我想死的大稿子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