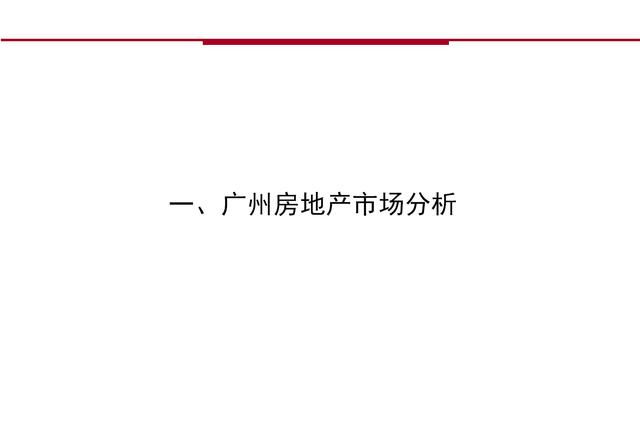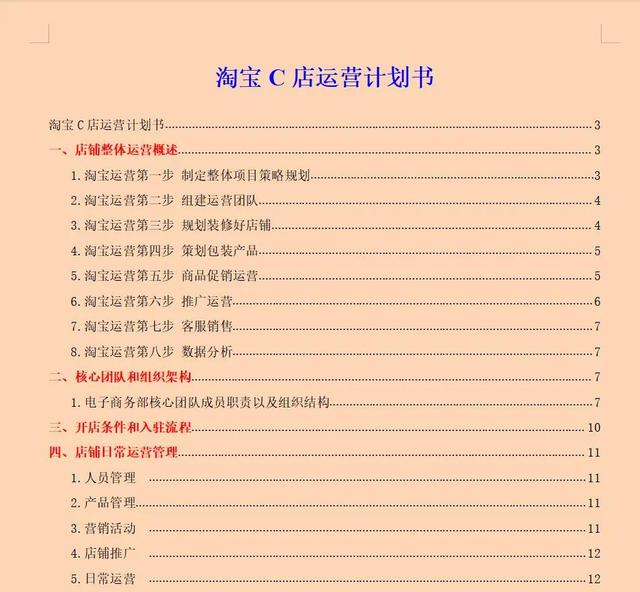从火车站开出来的公交车,不论哪一趟,最靠近前门边的都是“捧哏专座”,坐在那里的乘客时不时地与司机闲聊,一唱一和地逗闷子,也提醒你已经来到了“中国哏都”——天津。行至泰安道站,公交车在原名维多利亚花园的解放北园吐出人来,繁盛的花木提醒人们,已经到了百多年前英租界的地面了。
面朝海河、东临泰安道(咪哆士道)、南倚解放北路(维多利亚路)的利顺德大饭店(Astor Hotel)也“盘踞”于此已逾一个半世纪。对于这座可以住的博物馆,坊间有诸多离谱传言:据说住在某个特定房间会鬼压床、门可以自己开,甚至能听见女人的哭声——其实,这是老房子的荣誉:不闹鬼,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历史悠久。
利顺德夜景 (孟慧忠/图)
利顺德的闹鬼传闻有待“考证”,但悠久历史却不容置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放口岸,东至海河、西至今大沽路、北至营口道、南至彰德道的约3平方公里土地成为英租界。自1860年至1902年,美法德日俄意奥比步英国后尘,纷至沓来,强划租界共近15平方公里;冒险家、富商、政客、传教士……来此地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营建银行、商店、花园、办公楼、娱乐场、医院、学校、洋房、别墅——当然还有饭店。
1863年,两年前由沪来津的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殷森德(John Innocent)与英国女王驻津代表吉布逊签订租约,以600两纹银租下19.9英亩土地,在土地最南端的海河边滩涂上建立了印度风格的饭店和货栈,被戏称为“泥屋”,亦即今日利顺德的雏形。
只可惜“泥屋”如今已无任何图像资料了,作为华夏第一涉外饭店,这里吸引了普鲁士副领事馆、德意志帝国领事馆、日本领事馆陆续迁入;还特别受到“李中堂”的青睐——1870年,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设在天津的直总官衙取代总理衙门,成为实际的外交部,更让天津成为大清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和外交中心,提升天津的接待水平,成为他心心念念的问题——他催促的是自己的外事顾问、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古斯塔夫·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
1883年左右,英国人乔治·瑞德(George Ritter)买下饭店后,与德璀琳、商会董事长狄金生、怡和洋行买办马歇尔、梁炎卿等扩建饭店,并改名利顺德。这座于1886年亮相津门的维多利亚风格三层饭店增加了一座哥特风格的瞭望塔,颇具中世纪遗风,今天从解放北园望向利顺德,第一眼就能看到它仿若巧克力饼干的“雄姿”,亦即利顺德百余年岁月的标志。
从解放北园望向利顺德 (孟慧忠/图)
从瞭望塔西侧的木转门,就像那些从1886年起一直从这里转进饭店的历史名人那样走入利顺德老大堂,门外的明媚阳光与大堂内的暖黄灯光被木门的磨砂玻璃混合成变幻不定的暧昧光影,仿佛进入时光隧道,尤其是木转门上的“EST.1863”铭牌,和铺上厚厚手工地毯走上去仍会吱嘎作响的木楼梯,提示人们已经步入历史现场。
利顺德与它的建设者们,甚至住客们,也就在此地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作为利顺德的股东,德璀琳控制天津海关税务司达22年之久,还在1878年于维多利亚道创办天津海关书信馆,同年首发中国第一套邮票,即5分银的大龙邮票;于1897年改名大清邮政津局的书信馆,如今还在解放北路上,以天津邮政博物馆的“姿态”,展现着砖雕和拱形门窗的华美。同样也在维多利亚道上的天津印字馆,堪称与利顺德近在咫尺,由德璀琳、殷森德、狄金生等创建,在今天也展现着“方格控”的外立面。1883年,利顺德为北洋水师投资建造“利顺号”辅助舰艇,德璀琳之婿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on)还参加过甲午战争。
天津也就在此时成为一座因租界而崛起的城市。喜晴雨轩主《津桥蝶影录》言,开埠前,天津“只不过是一个繁盛一点的县治罢了。自从有清咸丰十年,与英国订了续约,开为商埠以来,渐渐的改了从前顽固不化鄙陋偏邑的面目”。1888年11月3日《中国时报》亦载:“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
还是德璀琳,1899年开春,他就已经与应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要求来津的英国墨林矿业公司工程师赫伯特·胡佛相熟了,之后他们还一起“骗占”了开平矿务局。胡佛并非典型的“事少钱多离家近”——他不在利顺德“斜对门”、泰安道东侧的开滦矿务局工作——1912年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和滦州矿务有限公司在激烈竞争后磋商合并,1919年才建立了威严的开滦矿务局大厦,当然和附近1903年建造的安立甘教堂比起来,它还是“小字辈”。直至1935年这座如同童话小城堡的孤独教堂被毁、1936年又再重建之时,居津三载的胡佛早已离开,甚至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第31任美国总统。
初到天津,24岁的胡佛和妻子露·亨利,“沐浴在利顺德饭店那一缕月光之下,沿着古老天津那烛光映照的街道上漫步的美妙时刻,周围香烟袅袅,耳畔响起春节那异乡的隆隆乐声,舞龙队伍擦肩而过”(《赫伯特·胡佛的成功之路》)——和一年后天津被围27天的境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胡佛已经离开利顺德住到五大道,并没有因义和团与列强激战、利顺德部分被毁而有性命之虞,不然美国历史恐怕要被改写——但著名的望海楼教堂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解放北路华俄道胜银行旧址 (孟慧忠/图)
屹立在海河边的望海楼又名圣母德胜教堂,然而建成仅一年,1870年四五月间就因“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死孩童作药材”的颇具“叫魂”色彩的一系列传言和冲突而烧毁。这边厢火烧望海楼的天津教案被写入近代史,那边厢曾国藩的幕僚一边吐槽天津“华夷杂处、市侩充塞,故城市全无清雅之气”,一边畅游紫竹林租界、吃洋点心、打弹子球、登火轮船,过足洋瘾——开埠后,外国人修建的第一个码头即紫竹林码头,这地界也是当年极富盛名的西洋景。
火烧望海楼后,英法侨民深感不安,教会活动逐渐向租界内转移,两年后比邻书信馆、坐落于英法租界交界处紫竹林村的圣路易堂(紫竹林教堂)建成,青砖木外立面饰以中华传统砖雕,内部祭台两侧据说设有法王路易九世和圣女贞德的塑像——和同一时期因巴黎公社而矗立在蒙马特之巅的圣心教堂一样。1900年义和团“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的“教堂破坏运动”中,紫竹林教堂因在租界中而幸免于难,而望海楼则第二次被焚毁——今日之正中高耸塔楼、远望如同笔架的哥特风格样貌,是1903年用庚款按原样重建的。
和教堂一起进入民国时代的还有各行各业,和各种人。英国人布莱恩·鲍尔的回忆录《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记:“军阀们将天津城围了起来,为争夺铁路而不停地厮杀、混战。天津东火车站时而被这个军阀占领,时而又被另一个军阀占领。与此同时,外国列强的军队不断增加。那是一个人力车夫和沿街叫卖的小贩没有任何价值的年代”——各行各业只能向租界中发展,才能存活,才能繁荣。
清末民初,中国政坛风云迭起,权力更替频繁,下野的军阀、官僚、政客甚至皇帝,都跑到天津这个“后台”藏身避风,一旦时机成熟,再伺机返回“前台”北京,粉墨登场。五大道1.28平方公里、23条道路、2000多座建筑中寓居两任总统、七位总理、百余总长、督军、省市长,更以姿态万千的西式建筑构成今日深幽宁静的街区风格;而同样肩负避难或谋权任务的利顺德,亦因“各种人”而成为近代天津风云变幻的见证地。
利顺德老大堂,充满怀旧气息。 (孟慧忠/图)
从利顺德老大堂向左拐的泰晤士厅,傍晚时分喧闹异常,好像赵四小姐仍然在这里摆设盛宴,来庆祝自己的24岁生日。她不常住这里——1924年,张学良以张作霖五夫人张寿懿名义购入法租界32号路(赤峰道78号)折中主义风格洋房,与赵四小姐住至1931年。利顺德闹鬼女人的哭声不会来自她,自然也不会来自婉容:居津张园和静园期间,每逢金秋时节,“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浑身散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的“皇上”与奇装异服的“皇后”必至利顺德歌舞,常至翌日丑时方归。在利顺德,溥仪还曾给随员都点上一杯咖啡,大谈特谈“喝咖啡的学问”。
女人的哭声也不会是首位女性环球旅行家阿洛哈(Aloha)发出的,尽管她1924年8月跟随老公瓦尔特·范德维尔(Walter Wanderwell)来到天津,曾入住饭店411号房。“如今”,她的隔壁“是”班禅十世,楼下“住”着陈嘉庚,二楼则“是”顾维钧的房间,还有孙中山、黎元洪、曹锟、蔡锷、黄兴、梅兰芳、马连良、傅作义、徐世昌等“友邻”——利顺德的名人房外皆有铭牌,记述名人与饭店的过往渊源。按“牌”索骥,敲敲房门,看看他或她会不会来应门?
作为饭店股东之一的梁炎卿也有间房,但纪念20世纪利顺德最重要的董事长海维林(William O’Hara)的,却不是客房而是酒吧了——老大堂向右拐的海维林酒吧也很热闹,1924年海维林主持拆除北面山墙、建造一座四层砖木楼房,使整个饭店平面呈“E”字,在“E”的凹进处增设的可容纳300人的舞厅,即今日饭店里的维多利亚花园,正在举办婚礼,其他客人就只能在酒吧里品尝下午茶了。
曾在利顺德设宴的袁世凯不在这里吃下午茶,他和“皇上”都钟爱先在法租界、后在德租界营业的起士林,那些黄油焖乳鸽、德式牛扒、罐焖牛肉、红菜汤、蛋糕、巧克力和冰淇淋满足了达官贵人们“崇洋媚外”的肠胃,但其实利顺德的菜品并不逊色——从酒吧向客房区行进,1924年购入的美国首批、中国现存最古老OTIS电梯旁,就是利顺德博物馆的入口,在这座曾经由电机房、锅炉房、泵房、面包房、库房、隐蔽室等盘踞的地下室改建的利顺德博物馆中,就收藏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节庆时令的中西菜单、餐具,还有美国制造的首批数字机,它计算了饭店数不清的盈利——总计3000余件藏品,无声地讲述了利顺德所开风气之先:引进中国第一代电报、电话、电灯、电梯、自来水和消防设备,西洋音乐、话剧、时装秀、台球亦在饭店发端……
在博物馆第一展厅正中,展示着一把珍贵的银钥匙。1925年3月,全体股东决定特制一把银钥匙作为饭店权力的象征,授予海维林,直到他1952年将饭店和银钥匙移交天津政府,全家移居新西兰——虽然天津沦陷期间,他曾丧失权力,和所有英国股东一起被押送至山东潍县集中营,利顺德亦被改称“亚细亚饭店”,直至1945年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恢复利顺德之名。也是在日据时期,起士林和维格多利餐厅合并,迁至今日距利顺德颇近的小白楼店址——白色的店面让人联想起阿尔伯特·起士林(Albert Kiessling)为袁世凯贺寿做的大蛋糕,建筑正中还有一个“K”字,“K”的西点至今仍誉满京津。
起士林餐厅 (孟慧忠/图)
没有一家饭店可以代表一座城市的历史,但利顺德也许能。五次扩建、九次易主、饱经时代风雨——清王朝的倾颓、列强的殖民侵略、北洋政权的更迭、民国政府的起落、日寇侵略的劫难……利顺德可以被看作中国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浓缩象征;如果说多重文化共存的天津提供了一幅微缩世界空间地图,那利顺德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图例。
利顺德外的维多利亚花园已经改名,饭店内的维多利亚花园就更成为饭店内的“图例”。在巨大的英式玻璃穹顶下,午后阳光早已将昨晚婚礼的痕迹扫荡一空,在绿植、鲜花和两边走廊上留下斑驳光影,喧闹也被流水演奏出的旋律荡涤干净,服务生已经端上摆放三明治、司康及甜点的三叠架茶盘,配以伯爵茶或大吉岭茶——好馋。
海河今昔 (视觉中国/图)
从维多利亚花园穿过,从利顺德最北的新大堂走出来,海河就近在眼前了。这条天津人的母亲河,也是酷爱利顺德的溥仪1931年登上装有炸药桶的汽艇、换乘 “淡路丸”到东北的必经之路。好可惜,听不到他讲的咖啡学问了,也不知他在长春有没有怀念过天津的锅巴菜和煎饼果子。和他一样的那些曾在利顺德留下雪泥鸿爪的名人们都已经远去,只有安立甘教堂,还是那么孤独、矮小、灰头土脸,只有五大道和意风区荒废的小洋楼、丛生的杂草和破碎的楼梯,见证着往昔岁月。
太阳强烈地照射下,海河飘散出腥味,可在岸边围成一圈踢毽子的中年老男人们才不理会,他们专注地大笑大叫“漂亮!”——也听不出哏味。海河沿岸的城市面貌急速变化,只有望海楼教堂,还保持着旧时的模样,哪怕它因海河的裁弯取直而多次出现与河道的“视觉左右大挪移”,它150多岁的圆形“大眼睛”依然凝望向海河,也“凝望”向在利顺德中游弋逡巡的鬼魂——那鬼魂也许就是历史。
张亚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