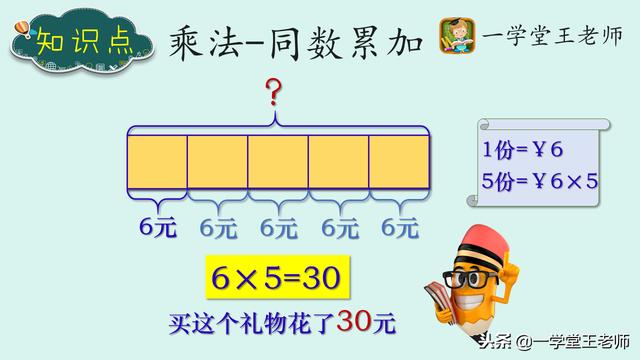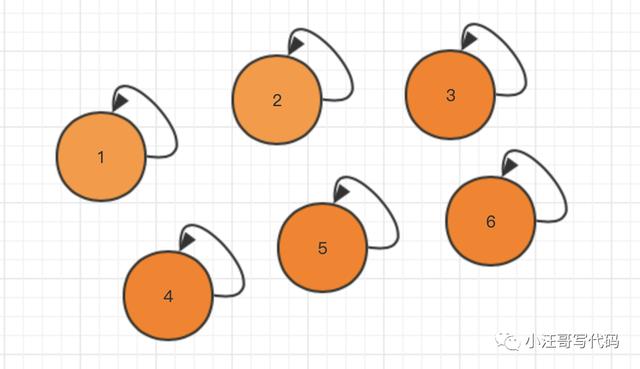作者:郭美金夏回
历史纪录片《故宫》以故宫为线索,以变化为切入点。通过12个篇章,讲述了明清六百年历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总结了历史发展中的得失,呈现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智慧。既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又展现了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点,引领观众探询历史的沧桑,追寻文化的根源。
纪录片《故宫》站在大历史的角度,跳出红墙绿瓦,讲述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事件。比如,通过中外文明的对比,可以展现中华民族的各种特点。《盛世年华》第八集讲述了英国使节马加尔尼访华的故事,强调中英互赠的礼物——玉如意和毛瑟枪,指出“枪和如意代表了各自的文化立场”,以此来说明中华民族的潜在实力和礼仪文明。比如,通过中外文明在风云变幻中的对比,可以总结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训。第六集《余晖》介绍了各国银矿枯竭导致银荒的变化,指出欧洲各国因银荒而初步建立起具有雏形的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而明朝因银荒而出现经济衰退。这证明了傲慢和保守思想的严重危害,总结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作为一部历史纪录片,如何引导观众全面、深入、清晰地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形成历史感,带动当代人对历史的追求和探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创作命题。”故宫用一种通俗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文化的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物与历史的巧妙结合,历史故事与主题曲的精彩对比。影片善于通过文物细节展现宏观历史。比如在第二集《姬野》中,利用故宫博物院文物李的《魏延附近的田园牧歌画卷》中的马匹,来表现早期武术运动的特点。同时,电影也通过现代科技让画卷中的人物动起来。比如《王者》第一集让《皇帝的胜利图》中的古人行走,配合激情的音乐和模拟的街头噪音,展现了历史上熙熙攘攘的街景。这种艺术处理方式显然打动了观众。有网友在弹幕中指出了画卷中穿粉红色衣服的男子的细节,可见动态画卷的表现方式引起了观众对明朝生活习俗的兴趣和关注。正如该片总导演吴智勇所说,“文物是证据,不是用来展示的”。但之前的故宫题材纪录片提到文物,似乎更多的是展示文物本身的制造工艺或艺术价值,而不是介绍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比如《故宫博物院藏书画》第七集,介绍了书画创作和保存的过程,但并没有重点讲述书画内容所揭示的客观世界。可见,故宫通过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更加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化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感性认识。
近年来,关于故宫的纪录片非常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宏大题材类、微观题材类和具体人物类。其中,《紫禁城》(2005)基于多个宏大主题,从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以及从宫殿到博物馆的演变过程等宏观角度进行叙事。,全面展示宫殿建筑、珍贵文物、人民命运、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故宫作为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此后,《当卢浮宫遇上故宫》(2010)和《故宫100》(2012)聚焦微观主题:前者解读不同空背景下的东西方艺术史,强调中西文明交流的宝贵价值;后者以故宫建筑的实用价值为基础,通过微纪录片的方式,用富有创意的解说和影像,表达宫殿建筑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故宫新事(2017)和我在故宫600年(2020)记录故宫文物工作者的日常工作。都以文物保护者的故事为重点,既展现了工匠精神,也展现了文物修复者对文物的理解——以物传情的物灵。
纵观本世纪的故宫题材纪录片,可以发现其发展脉络呈现出以下两个重要特征:不仅视野经历了“宏观-微观-宏观”的演变,而且表达也越来越年轻化。其中,视野的变化是从一开始的宽广视角,到具体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的阐释视角,再到文物保护者的人文个体视角,最后到中华民族的宏大视角。表现的年轻化趋势在电影《故宫100》《我在故宫修文物》《故宫》中尤为明显。《故宫100》单集时长不超过六分钟的微纪录片形式,满足了快节奏社会年轻人的观看需求。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年长的修复师的敬业精神和弟子们的青春活力,引起了众多年轻观众的共鸣。《故宫》片尾主题曲凭借歌手的社会影响力和兼具古风和流行元素的风格,极大地扩大了受众。
这两个特点的出现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首先,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宏观-微观”视野的演变。然而,世界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确立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身份,由此催生了“微观-宏观”视野的转换。其次,日新月异的消费社会也拉大了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收视习惯差异。纪录片创作者需要借助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吸引年轻观众,进一步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
回顾故宫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从整体的宏大印象,到具体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理念,到文物保护者的工匠精神和器物精神,再到故宫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个认知过程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比如《故宫》,不再只展示中华民族内部,而是着眼于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历史。借助年轻的表情,让观众看到中国文化的沧桑与辉煌。

上海文学评论专项基金特刊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