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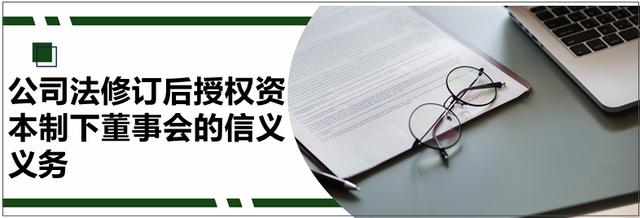
一、序言
授权资本制滥觞于英美法系,内涵在于股东会或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根据其商业判断,自主决定何时发行公司剩余股份。授权资本制可以降低股份有限公司设立门槛、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同时能够减少注册资本虚化的情况。英国在授权资本制实践一段时间后,基于制度和市场的成熟又发展出声明资本制。美国的授权资本制被日本吸收借鉴后,发展出折中授权资本制,并被我国台湾地区借鉴至今。对于我国能否从法定资本制转向授权资本制,是学界十几年来一直争辩的课题。随着服务型政府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和需求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12月2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也拟引入了授权资本制。然而,授权资本制在提高企业和市场运作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公司代理成本。授权资本制能否在实践中达到立法者引进该制度的初衷和期望,还有赖于公司法对董事会信义义务、监管和治理维度的构建。
二、授权资本制的域外实践
授权资本制起源于英美法系,[1]与采用法定资本制的国家相比,其差异取决于该国公司法律制度中公司治理结构与各方利益关注点不同。在选择授权资本制的国家中,更关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公司运转效率与全体股东利益。
美国在《示范公司法(1969年)》中取消最低资本规定后,各州公司法也相继取消了在公司章程中各类有关资本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仍保留最低资本的州法中,则只要求董事对瑕疵部分资本承担连带责任,而非提高公司成立条件。[2]英美法系建立了以公司董事会为中心的出资催缴机制,即董事会作为义务主体向出资瑕疵的股东催缴出资。[3]在英美法系的授权资本制下,股东通过公司章程授权的方式,提前规定董事会可自主发行的资本数量,董事会则可凭借商业判断,自主决定何时启动股权融资、抵御敌意收购等。
授权资本制在英国实践一段时间后被立法者扬弃,他们认为股东若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原因,可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来加强其控制权,而非仅通过授权资本制。[4]因此,英国在《公司法(2006年)》中放弃了授权资本制而转向声明资本制,声明资本制取消了章程对董事会发行资本总数的限额,董事会可自主决定发行股份的数量,赋予了董事会最大的自主决策权。然而,声明资本制并不适用于所有采用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因为是否采用声明资本制取决于该国的市场基础,市场规模庞大且复杂的国家往往不能盲从,转向声明资本制的变革,应建立在授权资本制已极为成熟的基础之上。
日本在1950年引入授权资本制,其本质是被限制的折中授权资本制,即公司设立时通过公司章程明确资本总额,并在发行部分缴足,未发行部分则授权给董事会伺机发行,法律对其发行的时间和比例进行限制。日本《商法》第166条规定,公司设立时发行的股份不得低于股份总数的四分之一;日本《公司法》第133条规定,发行被授权的股份不得超过已发行股份总数的四倍;日本《公司法》第201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被授权股份可只需经过董事会决议。日本学者认为,对授权资本制作此限制可以防止董事会滥用职权、违反董事会对股东的勤勉义务、防止原股东控制权被董事会无限制稀释。[5]日本的折中授权资本制也被我国台湾地区效仿沿用至今。然而,日本公司法律制度对授权资本制下董事会行为规制有待完善,有学者认为应通过内部监督和外部审计等方式完善公司内部治理体系。[6]
三、授权资本制在我国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
虽然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曾长期坚持法定资本制,但为了适应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在《公司法》《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中的个别条款可以看到授权资本制的影子。[7]我国从法定资本制转向授权资本制的变革曾被学界质疑,认为法定资本制必须被长期坚持,8但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市场环境不断完善,引入授权资本制的风险已被大大降低,在法律制度层面,我国已具备实施授权资本制的土壤。[9]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2021年12月24日,《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第97条规定,“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公司股份总数中设立时应发行股份数之外的部分,并可以对授权发行股份的期限和比例作出限制。”《修订草案》第164条规定,“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新股的,董事会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发行新股所代表的表决权数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代表的表决权总数百分之二十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修订草案》引入授权资本制,是为提高投融资效率并维护交易安全,深入总结企业注册资本制度改革成果,吸收借鉴国外公司法律制度经验,丰富完善公司资本制度。一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资本制,即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只需发行部分股份,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可以作出授权,由董事会根据公司运营的实际需要决定发行剩余股份。这样既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又给予了公司发行新股筹集资本的灵活性,并且能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虚化等问题的发生。[10]
四、我国引入授权资本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从公司的本质来看,股东和董事会系委托代理关系。公司的五个基本要素包括法人人格、有限责任、股份自由转让、董事会集中经营管理以及股东共有所有权。[11]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原理衍生出股东控制权、股东分红权和董事会集中经营管理的制度。在股东权利中,股东将对公司控制权的一部分授予董事会,却未授予分红权,而有限责任则成为股东向市场投入资金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公司是股东与董事会通过委托代理或信托关系形成的组织形式。因此,在立法实践中,公司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都应以股东收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在服务型政府转型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公司法的修订愈加褪去公法色彩,公司治理体系也愈加趋向于以作为受托人的董事会的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这也是以公司治理效率为主要价值追求的授权资本制被越来越多国家所推崇的原因。
从行为模式导致的决策偏差来看,董事会在增资决策中往往比股东会更为理性。在委托代理理论中,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和董事会对公司的管理权难免产生内生性矛盾。股东往往追求股利的变现收益,而董事会则更趋向于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因为股东在决策时受分红目标引导,常常基于经验判断,过分乐观的得出结论,在制度上也缺乏自我约束能力。[12]而作为受托人的董事会,在决策时要考虑公司内部监督、外部审计和法律的严格规定,因此在决策时就更趋近于理性。同时,从行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来看,董事会成员在决策时往往考虑社会地位因素,因此在决策时更容易从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我国公司法制度下,信托理论衍生的董事会信义义务已相对完善。在授权资本制下,股东会或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在授权额度范围内增发新股,一方面可以对股东决策进行纠偏,另一方面可以降低股权融资的程序性成本,这可以使公司资本制度被最大程度的利用。
此外,授权资本制更有利于公司融资。公司融资最主要的两个方式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相比之下,公司更青睐于股权融资。[13]因为债权融资往往受制于公司的现金流、产品市场和收益预期等因素,而授权资本制可使董事会凭借更专业的商业判断,决定是否发行公司剩余资本,大大提高了融资的效率和成功率。
五、强化授权资本制下董事会的信义义务
授权资本制下,董事会发行被授权资本可能导致原股东股权被稀释,特别是若董事会向关联方定向增发新股,可能使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动。同时,董事违反规定为他人取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可能导致原股东抽逃出资,使注册资本虚化。如前文所述,无论是从公司的委托代理理论还是信托理论出发,我国公司法修订从法定资本制转向授权资本制是有必要的。反观之,在授权资本制下董事会与公司和股东的关系成为核心问题。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明确董事会的信义义务,才能有效控制公司代理成本,确保授权资本制下各方市场主体利益平衡。
本次《修订草案》第180条在现行《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基础上细化了董事会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修订草案》第18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不得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本条对于董事会忠实义务的规定,要求董事会作为经营管理者,不得以变动公司控制权为目的,通过关联交易定向增发新股的手段发行被授权的股份;本条对于董事会勤勉义务的规定,要求董事会在发行被授权股份的过程中,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
若董事会在发行被授权股份时,董事会通过决议使公司为他人获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可能使公司的资金变为新股东的注册资本,这样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虚化。《修订草案》第174条新增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得为他人取得本公司的股份提供赠与、贷款、担保以及其他财务资助。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金融机构开展正常经营业务的除外。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子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违反前两款规定为他人取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条在董事会发行被授权股份,公司为他人取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提供了三个程序性条件,即章程事先授权、董事会以2/3表决通过,以及资助总金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0%。同时,本条还规定了董事会为他人获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的赔偿责任。
此外,引入授权资本制的根本动因在于公司对融资的机动性与便利性,该制度是基于股东会放权后董事会职能的扩张。因此,授权资本制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实践还离不开公司法在监管维度和治理维度的构建,还应同步董事成员的准入和推出机制,避免具有投机倾向的人员作为独立董事进入公司管理层中,并将发行被授权股份中未尽信义义务的董事驱逐出董事会。[14]
六、结 语
本次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授权资本制,是立法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背景下的一次勇敢且伟大的尝试。然而,授权资本制能否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还取决于股东会是否有信心通过决议或章程授权董事会发行公司的剩余股份,这一点还有赖于公司法对董事会信义义务和监管维度的进一步约束。笔者深知授权资本制法理基础之深,研究空间也还很大,本文仅以浅薄的角度进行论述,略显拙见。望《公司法修订草案》正式实施后,结合授权资本制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再续本文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参见范健、王建文:《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36页。
[2]参见〔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李存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37-38页。
[3]参见徐强胜、王亚霈:《从个人信用走向制度信用——基于公司法认缴制改革的观察》,载《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4]参见英保罗戴维斯、莎拉一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下册),罗培新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57-882页。
[5]参见〔日〕神田秀树:《公司法的理念》,朱大明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6]参见〔日〕山本为三郎:《日本公司法精解》朱大明等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7]参见拙著:《上市公司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研究》,载《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6月。
[8]参见甘培忠、吴韬:《论长期坚守我国法定资本制的核心价值》,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6期,第90-94页。
[9]参见白牧蓉、张嘉鑫:《<公司法>修订中的资本制度路径思辨——以委托代理理论构建我国授权资本制》,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4期,第124-127页。
[10]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21)》,2021年12月24日,载https://www.pkulaw.com/protocol/e899ca81868cef32509c4612191f68b7bdfb.html?keyword=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8修订草案%29》的说明%282021%29,最后访问:2022年1月17日。
[11]See: R Kraakman, J.Armour, etal., 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 A Comparativeand Functional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
[12]参见科林・F・凯莫勒、乔治・罗文斯坦、马修・拉宾主编:《行为经济学新进展》,贺京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64-88页。
[13]参见廖志敏、陈晓芳:《法律中的经济力量》,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4页。
[14]See: Steve Klemash, David Hunker, What Boards Need to Know About Shareholder Activisn,Based on their EY memorandum. 2021.

本文作者:

袁帅,德恒昆明办公室实习律师;工学学士、法律硕士、二级建造师。主要职业领域为房地产与建设工程、公司法律事务、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等。
指导合伙人:

郑宏宇,德恒昆明办公室合伙人、律师,财政部PPP专家库专家,中国政法大学PPP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主要执业领域为金融投资、建设工程、政府及公司法律事务、民商事诉讼等。
声明:
本文由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德恒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