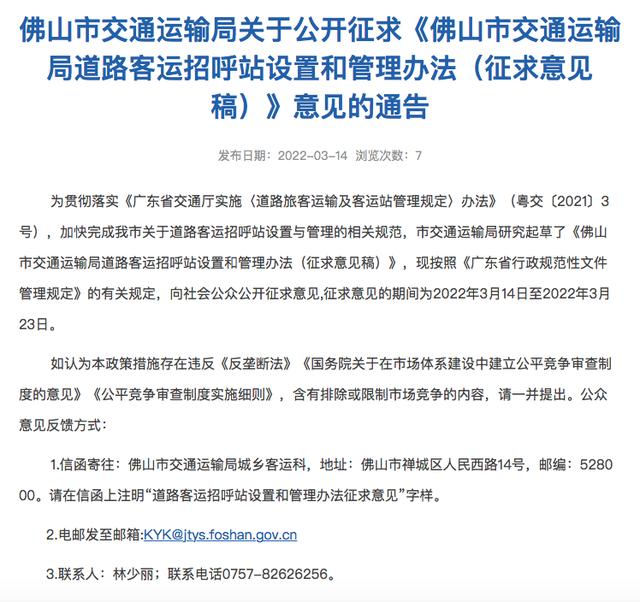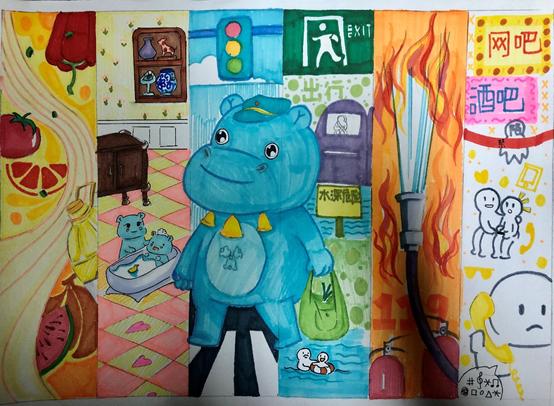9月30日,备受市场关注的《征信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发布。这是继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之后,又一重要的征信业新规。
事实上,自1月份《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以来,各界一直期待征信行业迎来更为明确的顶层设计。该《办法》明确,符合“依法采集、为金融等活动提供服务、识别和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三个维度的信息为信用信息,从事征信业务应当取得合法的征信业务资格。以“征信服务、信用服务、信用评分、信用评级、信用修复”等名义对外提供征信服务也将纳入管理范围,这意味着当前市场上部分机构的“回避”行为将得到更有效的监管。
正好

征信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有章可循
《办法》的出台恰逢其时。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保护法》),这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正式进入有法可依的新时代。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征信业的主管部门,按照上位法《人身保险法》的要求,在《条例》的基础上,颁布了与《人身保险法》相衔接的《办法》。
“征信行业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先行者,需要进一步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国内征信领域的适用。办法的出台可以促进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应用。”中华全国M&A协会信用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信用学会副会长刘新海向《金融时报》记者强调。在他看来,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先行者,征信行业需要进一步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国内征信领域的适用。《办法》的出台可以促进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应用。
从行业发展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平台频频曝出非法收集、滥用个人信息等负面新闻,给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刘新海指出,近年来,随着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从服务场景、数据类型到风险控制技术,征信和风险控制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数据出现,例如全球最大的征信机构易博睿在2020年年报中介绍,其90%的数据都是最近两年产生的;消费者的各种数据被随意滥用;信贷过程中数据应用的不透明,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数据泄露问题层出不穷,很多数据公司没有合规的概念等等。这些新问题给监管带来了诸多挑战。
“监管征信和信贷风险控制乱象的办法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他强调。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看来,此时出台《办法》不仅有利于整顿数据市场,加快我国数据市场发展,也有利于恢复征信市场秩序,促进构建科学、合理、稳定的征信体系。
“征信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办法》进一步规定了对信用信息和征信机构的监管,有助于提高征信行业信息流动的合法合规性。《办法》作为征信行业监管和建设的配套法律文件,有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信法律体系建设,促进了国家征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杨东强调。
明确定义信用信息
夯实行业发展基础
“这个办法的一大亮点就是什么是信用信息很明确。”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信用信息的定义主要采用了列举法——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用于判断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的各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和企业的身份、地址、交通、通信、债务、财产、支付、消费、生产经营、履行法律义务等信息,以及基于上述信息的分析评价信息。
但在官方发布的《办法》中,对信用信息的界定采用了“描述+类比”的方法——“合法采集”、“为金融等活动提供服务”、“识别和判断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被视为信用信息的三个维度。根据《办法》,基础信息、传统借贷信息等相关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析评估信息,都属于信用信息。
其中“其他相关信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替代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贷款信息以外的数据统称为替代数据。记者了解到,收集并使用替代数据来描述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正成为近年来国际上的新趋势。
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表示要将替代数据纳入信贷监管。2020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推进长三角征信一体化工作现场交流会,强调“当前,征信业的服务领域正逐步从银行信用向商业信用、信用相关替代数据领域拓展,市场化替代数据征信的互联互通是构建全覆盖社会征信体系的重要一步。信用信息正在成为依法实现金融数据、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共享互联的重要体制机制。”
"在全球范围内,信用信息的概念和内涵正在随着业务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刘新海向记者强调,《办法》的出台,给出了信用的定义,划清了行业的界限,既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有利于解决无序的行业问题。征信业务合规发展有利于征信行业健康成长,促进征信行业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2020年12月28日成立的第二家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朴道郑新,就以“另类数据”为目标。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朴道有限公司董事长韩表示,朴道、央行征信和百姓征信之间的关系是互补错位的,尤其是“朴道试图通过市场化机制收集个人征信以外的信用替代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和加工,以判断个人信用状况,帮助金融机构触达客户。
首家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百兴征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兴征信”)也在2021年年中工作会议上披露,公司备选数据源基本实现了公安、司法、工商、电力、税务、电信运营商、银联、航旅等基础数据源的广泛覆盖和数据的深度应用。
遵循“最低限度和必要”的原则
规范征信业务的全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将替代数据等信息视为信用信息,但不能出现“信用信息是一个篮子,什么都装在里面”的泛化问题。
此次《办法》明确,所谓信用信息,是指依据法律法规,通过为金融活动提供服务,可以用于判断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的各类信息。据此,闯红绿灯、频繁跳槽等“泛道德行为”被频繁列入失信名单,不仅涉嫌信息采集过度,也有违征信初衷。因此,《办法》要求信息采集遵循“最低限度、必要”的原则,这是为了纠正信用信息采集的滥用倾向。
除征信信息采集外,《办法》规范了征信业务的全过程。
比如在征信过程中,《办法》提高了规则的透明度。根据该政策,征信机构在提供信用报告等信用信息查询产品和服务时,应当客观展示被查询的信用信息内容,并对被查询的信用信息内容和专业术语进行说明;提供画像、评级、评级等评价产品和服务,应当制定评价标准,不得将与信息主体信用无关的要素作为评价标准。
上述资深业内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这与《人身保险法》第七条“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明确表明处理目的、方式和范围”的规定一脉相承,可以有效解决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黑箱”问题,确保信息主体获得公平的信用交易机会。
对于信用信息的使用,《办法》规定,信息使用者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应当有明确具体的目的,按照与信息主体约定的目的使用。业内专家特别强调,这与《人身保险法》中“个人信息的用途、方式、类型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的规定是一致的。”进一步解释,《办法》中对授权使用的限制,可以防止信用信息未经信息主体明确授权使用和‘一次授权、多次使用、长期使用’的情况发生,避免信息流动链条长带来的信息泄露风险。"
“有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即使是有执照的征信机构也不允许随意获取或调用相关信息。”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提醒记者。根据《规定》,有些信息属于限制信息收集,只有在充分告知信息主体收集和使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充分授权后,才能进行收集,如财产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等。,以及法律法规禁止采集的信息,严禁征信机构采集。
“《办法》对征信信息采集和应用的规范,有助于防止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不当处理和非法使用,提高征信活动的透明度,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石。”该人士强调。
完全“断开和直接连接”开始
行业告别“野蛮生长”[S2/]
随着替代数据被纳入征信监管,市场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从事“类信贷”业务的互联网平台将会怎样?
“在此之前,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不断深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双方的合作是合理的。”前述资深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可以为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支持,解决客户获取渠道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帮助中小金融机构弥补数据分析和建模能力的不足。
然而这种合作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金融机构可能缺乏独立性。受访专家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上述合作模式必然会围绕互联网平台的核心业务和利益链,进一步造成不同平台之间的相互封闭,出现事实上的信息垄断和信息孤岛。与此同时,一些互联网平台和金融机构采取了利息和费用共享的利润分成机制。利益驱动的合作伙伴可能倾向于过度信用信息主体,这将进一步造成整体违约风险。
监管机构对此一直保持警惕。针对上述问题,2020年底至2021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两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2021年4月底,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对13家互联网平台进行约谈;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通知,要求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个人征信业务实现全面“断直连”,即互联网平台只能通过合法合规的持牌征信机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金融机构只能与持牌个人征信机构合作获取个人征信服务。
【/s2/】《办法》的发布进一步明确了上述个人征信业务必须持牌经营。《办法》重申了《规定》,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机构的许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的“类信贷”业务会“一刀切”。对于很多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办法》提出“个人征信机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与其合作的信息提供者收集、整理、加工、分析个人信用信息的情况”。这被市场解读为“非持牌机构可能与征信机构合作实现合规展”。
据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分析,如果是非持牌机构向金融机构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或其画像、评分等,属于比较典型的征信业务,需要以获得牌照为前提,但如果非持牌机构向持牌征信机构提供此类信息,则仅属于前述的“信息提供”活动。
杨东认为,《办法》的出台意味着人民银行的监管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数据作为五大生产要素之一,其相关市场规则和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法治体系开始逐步完善,数字金融‘一放就乱’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强调,只有建立数字经济时代先进的监管体系,优化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才能引导我国数据市场、数据平台和数字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避免出现“一管就死”的现象,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事实上,很多之前从事“贷助”业务的平台已经开始寻求与持牌征信机构合作。根据《办法》,监管已经为这种转变留下了足够的“过渡期”。[/s2/]根据《办法》规定,2022年1月1日起,相关企业将有一年半的过渡期,这将是前述征信企业转型的“黄金期”。
“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为了鼓励征信行业的市场化发展,符合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征信需求现状。”杨东说。他认为,“美国和欧洲的征信市场发展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市场竞争过程。以上合作形式实际上是对个人征信市场严格监管的一种补充。我们应该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征信市场的巨大容量,促进有效竞争,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个人征信市场。”
“《办法》的发布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征信业‘野蛮生长’时代的结束。”前述资深业内人士强调。他认为,之前业内很多机构可能都在试探“合规”边界,一些非持牌机构反而可能“迈得更大”,造成“劣币驱逐良币”。随着规则的逐渐明晰,我国征信行业也将走上更加规范的发展道路。
本文来自《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