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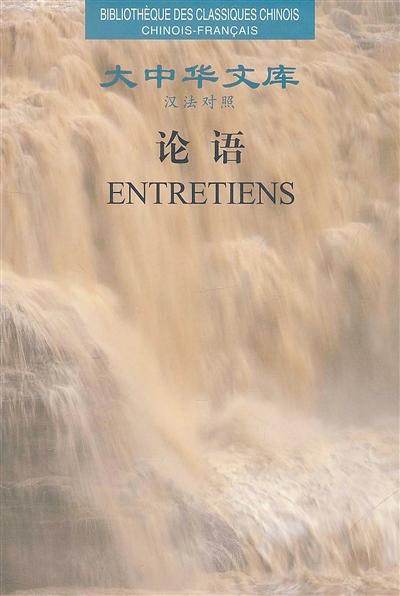
董强翻译了《论语》的封面。个人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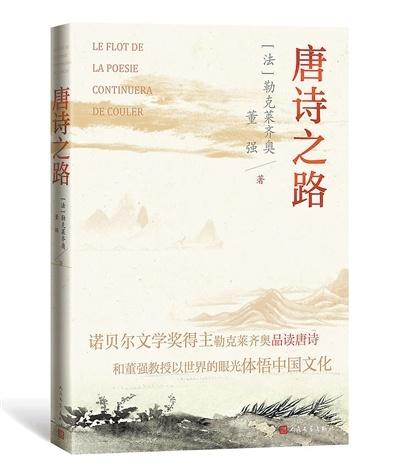
董强翻译了唐诗之路的封面。个人资料图片

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今天,有一个现象让翻译很沮丧,也让围观者很开心:机器可以通过“深度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智能。人们预测,就像阿尔法狗可以打败围棋世界冠军一样,终有一天,人工智能也可以通过不断的“深度学习”来完成高质量的翻译工作。不管人工智能能否完成高水平的翻译,我想提出一些关于“深度学习”的思考。
翻译人员需要进行“深度学习”
作为翻译,人——不是机器——也需要“深度学习”。译者往往被想象成静态的人,有固定的“层次”。我的看法是:恰恰相反。每一个译者的翻译都是一种挑战,一种自我提升,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这就是翻译的妙处,也是翻译更接近工匠和艺术家的地方,超出了理论的范畴。
这就涉及到译者的定义,即一个译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10多年前,我受托将《论语》翻译成法语。之前翻译过《李白诗选》,作为国礼送给法国总统。但是完整翻译《论语》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逐渐明白译者“深度学习”的必要性。
关于汉语,外国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汉语保存完好,一千多年来变化不大,中国人今天还能读到孔子。诚然,由于长期的传承,孔子的很多话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汉语,并以语录、警句、转喻等多种形式成功地“再现”在现代语言中。然而,超越语言上的这些例子,深入《论语》本身的大海,任何当代人都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专家的悉心指导,读《论语》是很难的。尤其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解读相互重叠,一句原话有多种解读。在最后的翻译中,即使译者可以在注释中添加其他解释,也只能选择一个文本。这就需要译者负责任地使用一种解释,在统一语气、文笔、思想、上下逻辑等的基础上,准确地用外语表达出来。
所以翻译《论语》,首先要学习《论语》,阅读各种版本。从字里行间读出一段话的基本意思,直到出现一个能让你信服的意思。这是一次历史的跨越。要把每个时代的解释搞得像地质层一样清晰,然后再选取出来,尽可能地把它们和《论语》中一些简单明了的不需要解释的句子“无缝连接”起来。换句话说,无缝连接的最佳解释在语境中最符合逻辑,最有说服力,是最佳选择。这是译者“深度学习”的结果,也是译者真正“责任制”的结果:当一个译者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最重要、最重要的责任不仅仅是语言或语法的准确性,还有译文内在逻辑的合理性。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翻译起码应该具备的能力。
译者的理想境界是成为创造者。
因此,译者成了集客观和主观于一身的高度负责的人。客观,因为译者同时也是学习者,所以必须学习尽可能客观的知识;主观,因为译者需要保证所有的感性、理性和理解,像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样做出“拿来”的决定。这是一个高度负责的选择。因此,译者的理想状态是成为作者或译文的创造者之一。
我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合著并由我翻译成中文的《唐诗之路》就是这种实践的结果。我们不是唐诗专家,但我们都有阅读和理解唐诗的经历。我相信我对唐诗的理解是高于很多外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的。所以,我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做了一个“保证”,这是一个道德的、智力的责任保证。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Leclerzio的作品在文学上影响深远空。他从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尤其是唐诗。所以他对唐诗的理解也是广泛的。他把唐诗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认为唐诗处于世界文学的顶峰。同时,他对唐代诗人的认识也是着眼于大局,在抓住根本特征后大大简化。
我把法文诗集命名为《诗的河流永不停息》,中文名为《唐诗之路》。河流和道路,一个是水,一个是土。诗歌的生生不息等于唐诗的生生不息,也表达了时间的连续性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变化过程,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理论意义上的“延伸”。在具体诗句的翻译上,我看了各种专家的讲解,用翻译《论语》的方法,提炼出一个我认为最可用的意思,翻译成法语。唯一不同的是,《唐诗之路》的译本经得起Le Clezio和法国出版社编辑的随时检验。事实上,精通英语的勒·克莱齐奥将许多唐诗英译本翻译成了法语。但经过比较,他和编辑都选择了我的汉译法直译,因为这样更“生动饱满”,“完全不一样”。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责任。
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并不是真正的“内容”专家。老一辈的翻译家,比如傅雷,往往和原作者有大量的书信往来,逐渐明白了一些自己不懂的东西。或者跟着外教,研究一个想法,一个作者再翻译。这说明即使是业内的专业翻译也要经过“深度学习”,但这个“深度学习”的过程在翻译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另一方面,很多翻译失败的原因是,人们误以为翻译有秘诀,一旦掌握,什么都可以翻译。
如果有“职业翻译家”,那应该是最擅长学习——而且“深度学习”的翻译家。因此,译者越是谦逊,就越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你越有责任感,在道德和知识上越有勇气,翻译的价值就越高。艺术大师安吉尔曾留下一句令人难忘的神秘话语:“素描是艺术的道德责任”,同样,翻译是文化交流的责任。这对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需要进行“深入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只有达到这个层次,译者才能成为真正的“媒介”和坚实的桥梁,成为不同文化的深入学习者和“摆渡人”。无论是翻译古代经典,还是新人新作,一个真正的翻译家都是在为一种文化中具有基础和象征意义的作品寻找最佳的“出口”,让读者感受到文化的浩瀚和它在当今世界的全新力量。
董强,1967年生,北京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燕京学堂特聘教授、法语系主任。2009年至2014年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2015年起担任该奖项组委会主席,同时担任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委。他被法兰西学院授予“法语国家金奖”。主要译著有《论语》、《黑马》的中译本,以及《培根论感觉的逻辑——德勒兹》、《小说艺术》、《乌合之众》的法译本。
《人民日报》(2022年03月20日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