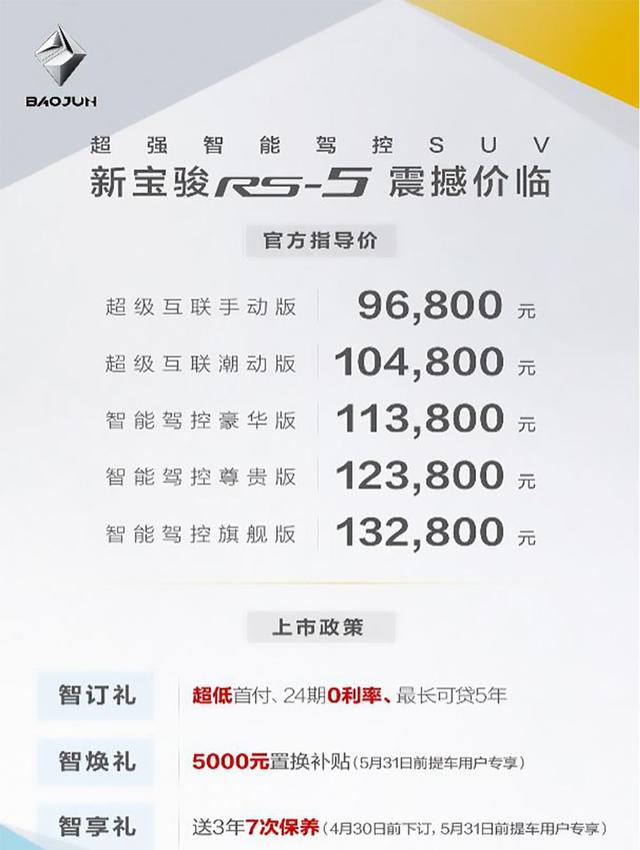我一直对邮局情有独钟。在我的印象中,一些特殊的行业都有自己的代表色。医院是白色的,消防队是红色的,邮局是绿色的。为什么邮局是绿色的,我一直不明白,但我一直认为绿色最配邮局,邮局就应该是绿色的。绿色总是给人希望。人们总是期待着信件的到来,或者说当他们期待信件到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满怀期待。
我小时候住的老街有一个邮局。就在我们大院大门的斜对面,一栋门窗刷成绿色的两层小楼,门口蹲着一个粗壮的邮箱,也是绿色的。这醒目的绿色是我对邮局的第一印象。从远处看,这个邮箱像是邮局的看门狗。然而,狗是黄色或黑色的。如果你没见过绿狗,你觉得说它是邮局的保管员更合适。可惜现在这样有时间感的邮筒已经不多见了。
这个邮局,曾经是一个老会馆的舞台,建在会馆的前面。清末改建成邮局,是老北京最早的邮局之一。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邮局,是在小学四年级。当时还卖报纸杂志的邮局把它放在柜台旁边的架子上,供人们浏览选择。我花了10.7美分买了一本在上海出版的月刊《青年文艺》。我觉得内容还不错,每个月都去那里买一本。初中的时候,父亲因病提前退休,工资锐减。我的姐姐当时正在内蒙古白雪皑皑的京包线上修铁路,每个月给家里寄30元钱来帮助家里。每个月我都会拿着汇款单,在这里取钱,顺便买青春文艺。每一次,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期待,我会感到温暖,因为《青春文艺》里有那些似是而非的故事,在那里神秘莫测地跳跃;那里隐约闪现着我姐姐的身影。
初中的时候看了一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红岩》。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虽然只是一部普通的黑白电影。在东北森林和雪域平原跋涉的邮差永远不会被忘记。我想象着,姐姐每个月寄回家的钱,我写给姐姐的每一封信,都像邮递员一样装在这样一个绿色的包裹里?都是长途跋涉还是风雨兼程?每次这样想的时候,心里都是满满的感慨——对邮局,对邮递员。
那时候,邮递员每天早上和下午两次挨家挨户投递信件和报纸。他们骑着自行车——也是绿色的——到大院门口,停下来,不下车,用脚踩着地面,抬起脖子,大声喊着有人要拿邮票!你会知道谁有汇款或者挂号信。下午放学后,我有时候特别期待邮递员给我家打电话要邮票!我就知道是我姐寄的钱。我会把父亲的邮票从家里的小盒子里拿出来,一阵风就跑到大门口。戳,就是印章。
除了给姐姐写信,我第一次给别人写信,是在高一的时候,给一个在别的学校读书的女同学。放学后,我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偷偷写完了信。当我走出学校,我不会乘公共汽车,而是走回家,因为在路上,我会经过一个邮局,在那里我会寄信。邮局是新建的,比我家住的老街的邮局大很多。夕阳透过大玻璃窗明亮地照耀着。刚来这里的时候,一切都显得陌生,但是绿色的邮箱和绿色的柜台又一次让我感到亲切,迅速拉近了我与它的距离。
我们开始交往三年,一直到高中毕业,几乎一周一次。每次,在教室里写一封信,在这里买一个信封和一张4分钱的邮票,贴好,把信放进邮局里靠墙立着的绿色大邮箱里,伴随着少年朦胧的感情和隐秘的忧虑。然后,等一会儿仔细看了邮箱很久,好像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只鸟,生怕它张开翅膀飞出邮箱,飞走了。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安静的邮箱,闪着绿光。宁静的邮局在黄昏时充满了金色的光芒,让我觉得如此美好,充满了想象和期待。
邮局的副产品是邮票。我就是从那时开始集邮的,一直到现在。贴在信封上的邮票真是五颜六色,就连一枚普通的4分8分的邮票也有很多品种。一开始,我把邮票和信封的一角剪在一起,泡在清水里,看着邮票和信封分开,就像小鸡从蛋壳里蹦出来一样,让我大吃一惊。然后,我像小鱼一样把邮票从水里捞出来,贴在玻璃窗上,看着风干的邮票像树叶一样渐渐从树上落下来,心里很激动。长大后,书信增多,使我积累的邮票与日俱增。不同年代的邮票,是一串脚印,串联起过去的日子,会让过去在一瞬间重现。邮票成了来自邮局的额外礼物。邮票是邮局里盛开的五颜六色的花朵。花开花落不断。每年都有新鲜的邮票问世,以至于邮局总是被郁郁葱葱的鲜花所包围。然后,它们通过邮局分发给我们许多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来到电影《红岩》中的东北林海雪原。奇怪的命运往往在于不可预测性。当上山下乡的高潮来临时,同学朋友都走了,去的北大荒是美丽的森林和雪域平原。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买了一堆信封和文具,约好给朋友和家人写信。在没有网络和微信的时代,手写书信这种古老而古典的方式,维系着彼此朴素而真挚的感情,让人期待而珍惜。而信件必须经过邮局和邮递员,这就使得邮局和邮递员如此不可或缺。只有这样,分散在世界各地朋友之间的信件才能到达你的手中。而邮局和信件,互为表里,互相转化,互相塑造。即使它们不是学者的珍贵书信,只是普通家庭父母的一封封简短的和平书信,也成为了过去时代的注脚和特征,让逝去的青春有了有形的物证。是邮局帮我们拿到并储存了这些信件,让我们的记忆没有随风飘散。邮局是我们青春情感和回忆的守护神。
那时,我来到一个新建的农场,周围是一片古老的荒地。夏天,野草在生长;冬天,下雪了。农场部只有简单的办公室泥屋,几顶帐篷,几个马架子,却不缺一个邮局和一个小土坯房,里面只有一个工人,胖乎乎的天津知青。我们所有的信件都应该是从她那里收到或发出的,每个知青都很了解她。但是,她不会知道,在她收到或发出的信件中,能发现多少神奇的内容,难以言表。他看了波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后说,他有一个叔叔叫尤利娅,因为起义和反动政府的斗争被迫流亡日本,患有思乡病。在他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让家人从基辅给他寄一片干栗子叶作为回复。记得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在给内蒙古插队的同学的信里,寄了一只蜻蜓那么大的蚊子。一个在吉林插队的同学,曾经送过我一块粘在文具上的当地奶酪。那时候,我们不吃冷的,不吃酸的,还没有尝到生活的真正滋味。我们没有像鲍斯托夫斯基的叔叔那样患乡愁。只有去邮局寄信取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份喜悦和期待。
这个土坯房里的小邮局,承载了我们青春里的很多苦、苦、甜。我不知道有多少封信要寄到那里,又有多少封信要回到那里,也不知道把农场知青的所有信件和包裹都算出来会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别看庙大,但神通大!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来到了天边,北京那么远,家那么远,朋友那么远,小小的邮局是唯一让我们和外界保持联系的桥梁。
上次去的时候给我妈寄钱了。那一年,父亲突然病逝,家里只剩下我老母亲。我回北京参加完葬礼后,就想尽办法转机回北京。最后,我得到了一个在北京当老师的机会。我回北大荒办理调动关系。春节前我回不了北京。我怕我妈担心,我怕我妈舍不得过年花钱。我跑到邮局,用30元钱给妈妈寄了一封信,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妈虽然不识字,但我相信她妈会找人读给她听的。那天,雪下得很大。不禁又想起了电影《红岩》。哪位邮差会把我的信装在包裹里,在茫茫大雪中奔波?长期以来,当我走进邮局时,我总是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因为有我想发送或接收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来自家里和朋友的信件,即使它们不是“三个月的战火之后”,同样的“一封家信胜过一吨黄金”。
命运一般,一直和邮局保持联系。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写完文章,总会有报纸、信件和稿费,还得去邮局收稿费,自己寄信和书。大约30年前,我家对面建了一个新邮局。因为经常去,所以对那里的工作人员比较熟悉。大部分是年轻女孩。如果他们偶尔忘记带零钱或者付款单上的名字写错了,他们会帮我处理。然后他们会笑着告诉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了哪些关于我的文章。这样,总是让我觉得亲切。有一次,我去邮局收稿费,柜台上坐着一个新来的女生。等她办手续的时候,我顺手在柜台上抄了几张纸,隔着柜台给她画了三张素描。接过钱后,小女孩突然对我说:“我看过你写的很多文章,你的文章是我中学时在语文课本上学的。”被夸,很有用,无望地给了她一张她认为最好的素描。她接过照片,笑着说:“我刚才看见你在画我!”
现在网络发达,很多邮件都是通过微信传递,信件数量锐减。大部分缴费改为银行转账,缴费单也锐减。还是那句话,总觉得只是虚拟的网信,一样的打印字迹,没有真实的墨迹,真的很无聊。缴费单是绿色的,上面有邮局的黑章,让你感受到邮局的存在。小小的缴费单上有邮局的印章,就像风吹过水面留下的涟漪。可能从小到大,邮局陪伴我太久了,我对邮局一直有很深的感情。邮局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升华了那些信件和缴费单,就像被火熄灭了一样。我知道这种升华,对我来说,是情感上的,是记忆中的,就像脚上的老茧,一天一天冒出来。
科技的发展往往考虑到时代的大发展,总是有意无意地伤害到人们最微妙的情感部分,或者以抚平甚至牺牲这些情感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如今,随着快递行业的高速发展,邮局日渐萎缩——当然,不能说是萎缩,只是暂时的角色转换和风景变换,就像旋转舞台上的过渡。就像现在多媒体的存在一样,传统的纸媒包括纸质书在受到冲击后依然存在,不会消亡,就像邮局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一样。顺便说一句,快件里没有邮票,这是发达的科技忽视伤害人们情感的又一个例子。只有邮局才会有如此色彩斑斓的邮票,集邮也就成为了一门世界艺术,想想古代马匹驰骋的驿站,曾经遍布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邮局,曾经矗立在街头的粗壮的绿色邮筒,还有电影《红岩》中扛着绿色邮包跋山涉水的邮递员...红尘中怎么会少了他们?他们曾经让我们对家人、朋友、远方充满了那么多的期待。谁送云锦书,只要有鱼鹅锦书,就有。
有一天,我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我抬起头,站在对面的架子前。这是一个前邮局工作人员。她看着我,显然认出了我。三十年前,她还只是个妙龄少女,风华正茂。现在,有一个和她一样年轻的女孩。她告诉我那是她女儿,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时间过得很快,她和邮局一起变老了。
另一个晚上,一个女人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然后,她马上转身,骑到我身边,把车停下,问:“你是肖小姐吗?”我点点头,没有认出她。她高兴地说:“长得像你!我二十年没见你了。你不记得了吗?那时候你常去我们邮局收款、寄书、寄信?”我立刻想起,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小姑娘!
我们站在街上聊了一会儿,就在夕阳融化金色的傍晚。我在想,如果没有邮局,过了这么多年,在茫茫人海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怎么能一眼认出对方呢?是邮局连接了南北,是邮局让陌生人之间的交流像水一样。

邮局!邮局!
2021年7月13日写于北京雨后。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