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浩/文过去一年,虽然中国经济表现尚可,但以中概股为代表的“新经济”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旧经济”在海外市场均出现断崖式下跌。当市场惊呼“中国的乞丐”和“悲惨的土地”时,对中国经济内在逻辑的解读出现了严重分歧,一些海外投行表示,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发生了变化。
分析了十几年的中国经济,深感理解中国经济从来都不容易,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更难理解中国经济。中美贸易战后,海外市场主流的困惑是,中国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看似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与政治体制大相径庭,东方价值观挑战甚至取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在西方观察家看来,如此“特立独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重新审视,而在另一派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在“胁迫”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贸易战”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看,郑永年教授领导的《系统中的市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化、结构化的视角去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不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过于纠结。这个视角融合了政治、经济、历史等多重视角,相信也会打开很多人一直存在于脑海中却难以系统描述的思想。
我个人很佩服郑教授很久了。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的时候,郑教授就在学校隔壁的东亚研究所工作,我也现场听过他的演讲。对于很多海外观察家来说,郑教授的观点不仅清晰,而且考虑到了海外受众了解中国的角度和程度。他是一位融合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大师。
从盐和铁理论开始
《Inside Market》开篇就提出了中国“特立独行”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受益于全球经济体系,却没有像很多西方学者预期的那样走上“英美市场化”的道路。与中国相比,“亚洲四小龙”的典型代表新加坡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几乎照搬英美制度,这被认为是其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时至今日,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腾飞,一直被视为英美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范例。李光耀还将他的自传《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命名为《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可见其中的苦与乐。
与新加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独特的模式,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仍然保持独特政治制度的核心结构性原因。虽然这个结论很容易下,但为什么这样的制度能与“市场经济”并驾齐驱,形成“中国特色”,这是本书致力于回答的问题。内部市场提供了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这本书提供的历史起点是汉武帝死后的一次大讨论。这一讨论在《盐铁论》中有所记载,是代表政府权力的法家和代表新兴精英的儒家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系统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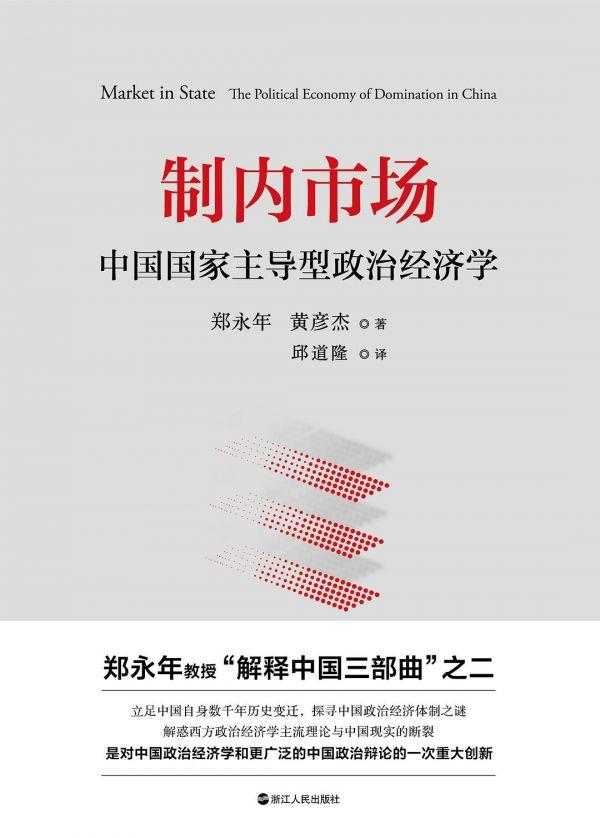
郑永年黄/作者
邱道龙/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国内市场”
为什么这样的讨论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走向。汉武帝留下的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帝国和长期被战争消耗的虚弱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汉帝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再平衡”,不同社会阶层的声音因为强大君主的离去而变得活跃,这为大讨论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在这场大讨论中,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帝国听取了儒家来自相对基层的声音,这已经说明,政治最终会体现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的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也会带动相应阶层获得政治话语权。

这一讨论反映了几个特点。第一,法家更重视政府的关键作用,而儒家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二是儒家更注重操作性问题,法家更注重原则性问题;第三,不管讨论的立场是否一致,两派讨论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家强大,也就是“富裕强兵”。
其实这就引出了本书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基础。首先,作者提出了“两个市场”的概念,即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无国家干预的市场。法家更注重政府下的市场,即国家市场,比如统一征收盐税和铁税,可以帮助国家获得更多的财力,让人民安居乐业。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如果每个人都能过上充实的生活,那么国家也可以强大,这就体现了“市场行情”的重要性,即国家不干预市场。
但是,为了保持两个市场平稳运行,相互促进,基本上需要一个重心。这本书提出“政治高于经济,国家重于市场”,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关键特征,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传承下来。其实这也是“内部市场”的内涵——“内部市场”是中国漫长历史中一直在演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个体系中,市场不是一个自主的、自我调节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受国家治理的调节。
“国家”和“稳定”
从盐铁论讨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形成了两个立足点。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是一天建成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的内外挑战,但其根本内涵并没有改变,其发展道路仍然是通过改革提高竞争力,实现国家强大的最终目标。
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事件,比如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实都是期望在困境中得到解决,而且无论是改革还是改良,都无意寻求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而是希望实现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学者在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图景时,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和“稳定”在中国语境中的极端重要性。这个时候“经济”这个词就把国家和市场,东方和西方的差距画出来了。在东方国家的语境中,“经济”是“济民通天下”,市场是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中,“经济”就是通过供求的动态平衡,使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我不打算在这里把国家和市场,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区分提醒大家,完全以西方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和市场,很可能会陷入逻辑无法自洽的困境。
“层级”和“激励”
国内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中国的市场分为三个层次——基层、中层和国家级。这样的分层可以帮助我们澄清很多困惑。具体来说,国家层面是顶层,中观层面是市场与国家的互动——比如国有与民营联合经营部门或代理国家利益的民营部门,底层是区域和地方基层市场。
通过这种分层,我们可以通过“动机”来理解每一个分层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基层来说,他们很少关心宏观经济图景,但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商业环境。他们的“动机”更纯粹,也更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概念,他们的根本动机是利润最大化。西方学者在义乌小商品城调研时,看到小生意如火如荼,斤斤计较,也充分理解了中国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但西方学者一旦参加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研讨会,就会被一些“奇怪”的语言所迷惑,进而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怀疑。
如果按照本书中市场分层的视角,可以理解不同分层的不同立场和动机,相信研究者会更容易找到立足点。
在郑教授看来,中国的市场分层虽然有鲜明的特点,但也不是没有互动。比如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萌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互动。当时作为基层农民的参与者,他们并没有思考“大责任”的政治含义,他们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生存。但这样的基层行动在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后,很快推广到全国,并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一个基本制度,这是基层与国家层面的生动互动。
“鸡鸭讲”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理解“内部市场”的两个维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以国家为核心的不断演变的政治经济体系。从市场框架来看,这是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多元市场结构,但核心仍是国家层面。显然,在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国家和皇权其实是很难区分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层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即使上述逻辑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中国读者的认同,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与鸭讲鸡”的现实困境。当一个人无法理解中国的帝国历史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时,那本书的内容只能在国内销售,而这样的“国内销售”并不能解决外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困惑。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东方语境下,很多事情不需要“说清楚”,也不需要“说明白”;在西方语境下,不能“说清楚”或“说清楚”的事情,更值得“打破砂锅问到底”。
就经济学而言,数量模型研究已经成为主流,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内市场”可能很难完美复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往往不仅反映基于供求关系的经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反映了政策意图。
比如去年“电荒”蔓延的时候,发电用的动力煤价格如何计算,就是一个经典的中国语境问题。在期货市场上,动力煤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预期甚至是炒作的程度,而坑口价格则反映了当天的实际供求情况。而国有煤企可以以低于“市场价”的水平向供电厂提供“廉价”的动力煤,使电厂可以完全无视市场煤价的上涨幅度,以固定价格向工业企业供电。
在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图景显得非常突兀。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某种程度上,这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最后警告”——那些想在保民生之际大捞一笔的人,最终都要付出沉重的市场代价。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期货价格腰斩,给一群虔诚于市场逻辑的投资者上了一堂政治经济学课。
东方和西方似乎并不接近
事实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这种国家(政府)与市场的拉锯战从未停止过。即使在今天,政治仍然高于市场,国家仍然是经济的重心。从这个角度看,本书的讨论具有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对于不能理解或者不想理解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西方研究者来说,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有限的。一方面,西方研究者通过研究中国不同特征的市场主体,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很难将这样的独特性融入到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数学模型中。所以,这种东方“独特的感觉”就成了只有对东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群体才能理解的领地。这种差距加深并拉开了东西方的认知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内部市场在更高的层面上解释了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独特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但与此同时,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西方主流学术界为中国经济研究“搔首弄姿”仍将是一种常态。经过多年的交流,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似乎并没有真正拉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