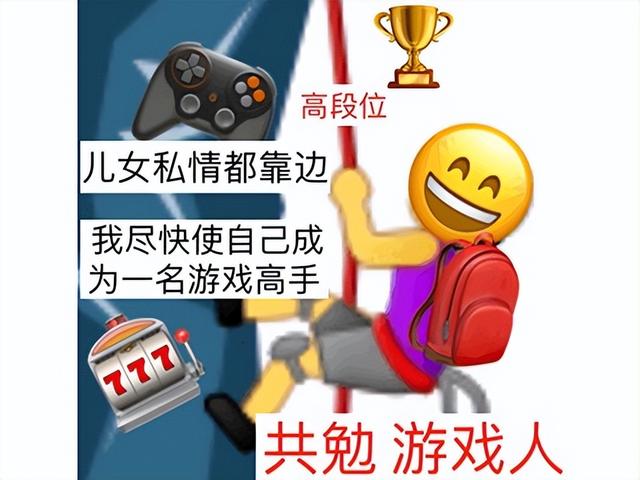今年的年轻人都在“和亲戚离婚”。不愿意回家过年,拒绝办婚礼,没有亲人联系方式。如果不是血缘,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见几次面。
他们大多在独生子女的环境中长大,父母之间那种断骨接筋的情感自然感受不到。从乡镇到城市的地域迁移后,没有家庭聚集的环境。父母以前靠亲戚做的事,他们也可以通过雇佣关系解决。很多人常年在外学习工作,有些亲戚几乎记不住名字。
与此同时,“自我”的外壳逐渐变得坚硬,有些亲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负担。当彼此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不熟悉的几代人强行维持关系是“痛苦”的。最终,有些人选择断绝亲戚关系,逃离。
我们找了几个正在或已经离婚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的离婚故事。我们并不打算对“离婚”这一现象进行评判,而是想知道离婚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我们发现有些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些被切断了,但更多的是年轻人,需要重新建立与他人的界限。他们在“断绝”一些亲属关系的同时,也在建立新的人际规则,自己选择新的“家庭”,从而形成新的亲密单位。
文| 冯
编辑| 楚明
只有四个亲戚被邀请参加我的婚礼。
时至今日,父亲过年回老家,依然会被亲戚朋友质问,为什么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我的婚礼。他仍陷在我离婚的泥潭中。但我的婚礼,对我来说,是我“建国之战”的一次胜利。我的“离婚”有两个层面,包括父母和亲人。“断”的方法是逐渐养成疏离感。
我18岁离开家去上大学。从那以后,在父母眼里,我已经到了成长停滞的状态。生理上,我们相隔200多公里,但心理上,他们对我的认知还停留在18岁之前。
我父母都是教育行业的从业者,控制欲很强。我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从来不调皮捣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后来,我自然去了清华。考上清华也没那么光彩了。这个结果在我父母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另一方面,我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孩子,小时候也很乖——这是父母“驯化”的结果”。只有“听话”,才能得到父母的“奖励”。在我成年之前,我对对错的判断完全取决于父母的判断。直到27岁博士毕业,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2012年,博士毕业,面临两座大山:职业选择和婚姻。学业有成,但父母出于“稳定”的考虑,希望我去国企工作。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对“不稳定”的焦虑,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和引导。每当我说出我的想法,我很快就会被他的判断所压倒。于是,我们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以他的一句“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我为什么管不了你”结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只是在传达自己的焦虑,希望控制我的生活,却从来没有真正听到我的声音——九年的身体和心理距离,我的意识已经离开了他们,开始成长。
恋爱婚姻也是如此。我在工作上安顿下来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次相亲,女孩是他们的关系找到的,算是世俗意义上的“门当户对”。相亲的流程是双方父母先见面,确认“匹配”,再安排子女见面。然后未经我允许,他们居然背着我把对方父母撮合成“准公婆”,约定一起过年。知道了这些,我忍不住了。在这次对峙中,我妈一遍又一遍地说:“自由恋爱遇到骗子怎么办?”她很焦虑。当时我无法具体表达那种苦恼,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和他们的冲突。
这种状态会持续到2015年。借着一次松散谈话的机会,我利用一个人留在北京过年的机会,坚决执行。
父亲说:“过年要有习俗”。于是我发明了一个新习俗——年夜饭是一碗泡面。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开车在北京四环逛了一圈,过了四环直奔宜家,又吃了一顿“瑞典餐”,这是我一个人留在北京过年的“新民俗”。
我知道,对于一个思想守旧的父亲来说,儿子不回来过春节,这个家人团聚的日子,有多大的“杀伤力”。
2022年是我实施“新民俗学”的第七个年头。开在四环上,感觉蝙蝠侠开着他的黑色大轮摩托,在他的城市和地盘巡逻。当车辆前进时,它的头会循环计数今年它做过哪些叛逆的“坏事”。叛逆给我带来了“好孩子”时期从未有过的快感。在感觉“背叛”了家人之后,我的自由正在一点点被夺回。

电视剧《赢家就是正义》
后来,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女孩。在和她确立关系之前,我假装很轻松的问她“和家人的关系是不是彻底断了?”“她很快领会了我的潜台词,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那就是我们在不受对方干扰的情况下,凭自己的独立意识做出了选择。
从2015年开始,我和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少。偶尔接触只是例行汇报。恋爱初期,我妈试探性的问我女朋友的情况,感受我的情绪。她硬生生咽下了“她不可能是骗子”这句话——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34岁那年,我决定举行婚礼,婚礼在海外举行。婚礼没有礼金,我决定谁参加婚礼。为了表示对父母家庭的尊重,我只邀请了双方各两名亲属作为代表。我把这个决定以“通知”的形式传达给了父亲。他知道我的态度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飞往国外参加婚礼之前,我包了一辆大巴,把参加婚礼的人送到首都机场。我父亲帮我做了一些召集朋友和亲戚的工作。大巴到了首都机场,他把组织好的“小蜜蜂”递给我,说“轮到你抓指挥棒了”。
收到“小蜜蜂”后,我说:“接下来,请按照我的指示来”。那一刻,我觉得很庄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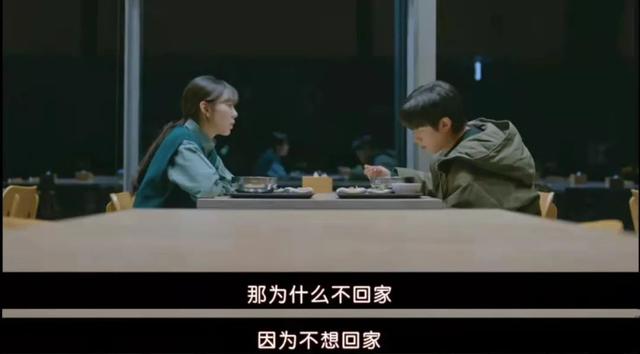
姐姐已经“消失”了,我觉得我亏欠她。
姐姐不喜欢叫,她不喜欢叫任何人,包括父母。我喜欢打电话,一天一次,先给我父亲,然后给我母亲。
姐姐什么时候“断交”的?我不知道,但好像有一些是因为我父亲而被打开的。我妹妹很年轻,今年才25岁,但是已经结婚怀孕了。在谈恋爱的阶段,大家对她未来的老公一无所知。我妹妹没有谈及任何关于他的信息。除此之外,她很少主动联系父母。我猜是因为她不想让父母干涉她的感情生活。但是我爸妈很担心,“我姐的男朋友是干什么的?”他们总是问我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
事情进展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有一天,我姐突然跟我爸说她要结婚了,我家人都惊呆了。大概在那之后,矛盾变得更加肉眼可见。我姐觉得结婚是她自己的事,我不想家人干涉。我父亲认为我家在还没有太了解男朋友的情况下就结婚是草率的。爸爸妈妈想让妹妹回家摆桌子,但是妹妹坚持一切从简,因为和家里亲戚不熟。我和姐姐约好周六和父亲“见公婆”,但父亲认为这种单方面的决定不尊重他。爸爸勃然大怒,说:“没空!」
之后我爸就不关注我姐了。不再联系,不再说话。虽然他们以前只有微弱的联系,但我爸总是主动说话。但这一次,冷战持续了半年,似乎没有尽头。
和我不一样,我妹妹不喜欢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她的父母。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市里首屈一指的寄宿学校。之后整个青春期都在离家一个半小时车程的郊区读书,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特别想家。父亲开车把我送到校车的接送点,把我送上了车,而我在下面眼泪汪汪地看着他。对我来说,离开家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说分离焦虑也不为过。每次到了学校,我都要找个公用电话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很安全。因为寄宿,有时候我会把爸爸给我带的那瓶水喝完留着,因为我会觉得那瓶水让我很安心。
我姐姐不一样。她只考上了镇上的公立初中。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没有多次去接她,因为她离家近,大部分时间她姐姐都是一个人回家。有一次,暗恋她的男生骑着自行车跟着妹妹到我们小区门口,我爸上前把那家伙赶走。初中毕业后,姐姐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人。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英语很差,数学很好。她不喜欢和我父母交流。周六,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电脑上和YY公会的人聊天,表演节目。离开房间后,她又变得沉默了。我妹妹的青春期似乎不太快乐。我们完全分开了。高中的时候,妹妹考上了私立寄宿学校,但是她已经不喜欢打电话汇报日常生活了。
我对我妹妹一生的了解是空白的。回想起来,很多时候我是主角,妹妹连配角都不是,好像消失了一样。只记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餐桌上争抢食物,比如只剩下一个鸡腿给我吃。印象最深的交集发生在小学四年级。我去了一个军训夏令营。起初,我踌躇满志,带着行李去了营地。但是爸妈要走的时候,我哭着抱着爸妈说我要回家了。在一个办公室里,指导员很严厉,他说;“走了就是逃兵!”但我还是哭了,我真的不想睡在帐篷里。爸爸妈妈想了一个好办法,让姐姐给弟弟当兵。他们把我带回家,把我妹妹送到了营地。后来在洁英相册里看到一张姐姐牵着一只大狼狗的照片,很有气势,很壮。现在想起来突然想哭,觉得自己欠姐姐一笔债。
我们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但是我妹妹真的不喜欢和我父母交流。她回家的时候还是兴高采烈的,但是她拒绝打电话。爸爸不是坏人,只是喜欢挖苦妹妹,这是他的特长。私底下,父亲多次跟我说,“说白了,你就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今年妹妹和新婚丈夫没有像我们一样回粤北的村子过年。
除夕的气氛很好。虽然妹妹不见了,但不影响父亲大声开玩笑。晚饭和下午茶时间,两个回老家的表兄弟开始给我爸讲他们和叔叔分手的故事。“直接把我们扔下高速”“对,对,还有一次,我已经跟他(叔叔)说了不要送顺丰,送顺丰会很贵的,但是最后还是故意送顺丰的。”两个堂兄弟零零碎碎地说,爸爸默默地听着。
几年前,我的表兄弟们因为各种原因和他们的父亲分手了。之后父亲开始扮演“贴心大叔”的角色,经常私下帮他们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决心不和他交流。现在我们自己买车,在大城市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等这么一天。”其中一个表亲说。
“哈?没办法。”我爸的脸开始变红。我不知道他是喝醉了还是生气了。“至少他是你的亲生爸爸。”表哥随后开始解释他们离婚的原因,我爸坐不住了。我坐在餐桌的一角,默默地看着这一切。我知道,我爸已经不能像几年前那样轻易对我的堂兄妹感同身受了,因为现在,他的女儿也在逃亡,就像我的堂兄妹一样。

土元电视剧《一切都好》
我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似乎不是巧合。在我家,为什么表亲都离婚了?现在轮到我妹妹了。叔叔的两个女儿跟奶奶住在农村,小儿子被带到东莞。卜儿的两个女儿和奶奶住在农村,他的小儿子把她们带到了深圳。我听说卜儿的两个表兄妹考上了深圳的一所大学,连学费都不用交。
团圆饭快结束的时候,爸爸爆发了。他拿起桌子站起来,骂了我妹妹一大堆难听的话,大概是“不孝”之类的。在父亲眼里,姐姐不打电话就是不孝顺,私下结婚怀孕就是不孝顺。然后我就一个人上楼了。我妈妈洗了一会儿盘子。沉默了很久,她从厨房里冲了出来,系着围裙,拿着锅铲,指着我爸爸流着泪,尖叫着:“你再骂我女儿试试。」
姐姐说,和亲人断绝关系后,她的生活好像“出水很难呼吸”,但她也说,“你开心不开心真的没什么区别,他们还是他们,我还是我”。
坦白说,我对我妹妹有些不理解。我可以很容易地打电话给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劝过姐姐,她说不行,“连走位仪式都不行?”“没有”。
我也很无奈。有时候在我面前帮姐姐,爸爸会大发雷霆。过年后看到姐夫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姐姐和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照片,觉得没有吵架的大年三十真的很幸福。“父权制”的破碎场景很残酷,爱我的父亲坐在那里叹气。他觉得现在全家都乱了。以后怎么和解,会不会有和解,是个问题。现在只希望妹妹能永远幸福。
除了父母,我不在乎任何亲人。
“避亲”大概是我整个春节最重要的关键词。虽然这种行为被家长批评为“不人道”。
2022年春节前,我和父亲商量,“要不我留在北京过春节?”说服他的理由是疫情严重,此时回国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父亲一脸尴尬,但家人告诉我,自从我提出不回家过年的想法后,父亲连饭都吃不下。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却要逃避。
我该如何描述我对春节回家的恐惧?更具体地说,是对复杂而又黏腻的血缘关系的恐惧。离我老家北京高铁三个小时。平日里,回家的次数不算少,但只有在春节,这几年抗拒回家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家有很多亲戚。一想到在外面忙了一整年,回家还要开一整天的“商务”模式,头皮都麻了。
整个春节,家里都是人。最夸张的时候,早上9点开门迎客,晚上10点后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家里一天要迎来5批亲友。我朋友甚至调侃道,“就你家这点线下流量,如果每个请客人的人都在拼多多砍一刀,一辆电动车应该能砍到手。」
在外忙了一整年,春节回家真的比上班还累。
我父母兄弟姐妹众多。他们生长在物质资源匮乏的五六十年代中原农村。兄弟姐妹们需要互相帮助来度过许多艰难的岁月。每次想到兄弟情,我妈总会给我讲大叔叔早早辍学,支持弟弟妹妹读书的故事。她还谈到30多年前,父亲的哥哥是如何照顾瘫痪在病床上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父亲),从而提醒我要感恩这些长辈,甚至给我灌输“受了委屈也要帮助别人”的价值观。
现在,父母的兄弟姐妹大多已经到了第三代。我父母的大部分兄弟姐妹现在都是五六个孩子的爷爷奶奶了。如果把这些子子孙孙加在一起,就是一个80多人的庞大家族。中原很重视亲情,父母也很珍惜手足之情,但这些关系到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就变质了。
每年过年后,妈妈就开始准备年货。从腊月二十六开始,一家人就开始每天庆祝汉人的节日。晚上收拾残局,白天打扫“战场”,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体力工作。我还在这边洗碗,我妈已经开始准备第二天的菜了,一边准备菜,一边抱怨自己太累了。这个时候,每当她来传达如何让自己受委屈,让别人开心的价值观,我都忍不住反驳。
家庭关系不像早些年那么简单了。到了第三代,父母的兄弟姐妹自然要偏袒自己的后代。表面上过年参观,进门就玩手机。有时候五六个孩子一起哭,头都快爆了;有些亲戚,几年前只见过一次面,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和十年前一样的话,尴尬得挠了挠脚趾头。有些亲戚可能出去过三次,但我不认识,因为经济上有些问题,偶然上门还得父母要求殷勤。另外,难免有些亲戚以打探别人的私事为乐,前脚打探别人的事,后脚就在饭桌上广而告之。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过年只是为了满足某些亲人的窥视欲。

土元电视剧《一切都好》
至于父母相濡以沫,伤筋动骨的感情,我一点亲人的经验都没有。有些亲戚,你这辈子不一定要见几次。除了父母,我真的不关心他们。
我父母已经60多岁了,价值观极其顽固。我已经放弃说服他们了。我的“离婚”只是心理上的。这几年几乎没有主动联系过任何亲戚。
整个春节,我极度疲惫的时候,离开一屋子客人,找了个理由背着电脑躲了出去。我不想在这样的环境下“假装商业微笑”。估计一下客人要走的时间,然后回家。父母忙的时候,我也忙不过来。我得回去帮忙。春节过后,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种不好的心情,回到北京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失。
回北京的前一天,送走了当天最后一批亲人,父母瘫在沙发上休息。在我收拾行李的时候,父亲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回家八九天了,却没有一天和我好好聊过天。看到我不高兴的脸,父亲终于放松了。“如果你明年春节不想回来,提前告诉我一声。”
也许明年,我就再也见不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


土元电视剧《暗恋橘生淮南》
退出家族群,我也不用再被亲戚评头论足了。
在“分手”之前,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里长大的。我家里大部分人都是知识分子。我爷爷奶奶和孩子关系很亲密,以至于我爸妈很信任我让我二姨照顾。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和父母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我二姨是一所小学的教学主任。她在判断大部分事务时总是有一套非黑即白的逻辑,这也成了我噩梦般童年的开始。
就她的主观喜好来说,我不属于传统意义上那种成绩好,温柔的“好女孩”。把她带到班主任门口,一边学习一边骂她,这是常有的事。印象中,班主任办公室位于楼梯口,也是学生上课的必经之地。我不记得小时候具体犯过什么错误,但是那种被人盯着看的感觉,想起来都很难受。
这种不适在2010年的一次旅行中达到了顶峰。今年,我住在美国的三姨回老家探亲,我陪她和她二姨参观了世博会。我三姨的老公在美国大学工作,她儿子在沃顿商学院读书。在这次旅行中,她无时无刻不在炫耀自己“海外家庭”的优越感,试图将我拉入她的阵营。我二姨希望通过她对我的不断控制来宣示她的“主权”。
这些年来,在家庭微信群里,在家庭聚会上,在表面和氛围下,暗流涌动。谁上了名校,总会再拉一个孩子出来踩;谁买了什么车,表面上的奉承和赞美,瞬间可能是另一种嘲讽;哪个家庭成员要结婚,婚礼的安排,对方的家庭背景,都要被这些亲戚“欣赏”很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无论做什么,似乎都会感受到评判的压力,真的让人窒息。后来我干脆退出了所有的家庭群。在必要的家庭聚会上,不喜欢的亲人直接视而不见,不予理睬,但整个世界都是干净的。
2017年和男朋友领证,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包括父母。在我心目中,领结婚证和办婚礼是两回事。领证只需要我们互相参加,但是婚礼涉及到对方的家庭。一旦我的亲戚知道了这件事,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就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我不想被任何人评判。
至于孩子,我们当初也约定了丁克。我没有勇气做出过小生活的决定。我见过太多原本和和气气的夫妻因为孩子的到来而跳脚。中国家庭有一个特点叫“隔代亲”。因为教育观念的不同,他们对老一辈不满。这种代际干扰,说白了就是一种负担。
但是我对宠物有无限的爱。最多的时候,我养了20多只猫。我可以在家呆很多天,陪着它们,观察每只猫的喜怒哀乐。与人类相比,动物要简单得多。

来源电影《租来的猫》
家不再是我唯一的港湾。
我的“离婚”是在12岁左右慢慢开始的。我今年24岁,亲戚大多没有联系方式,基本没有主动接近过。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我的父母。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两个人都在看着一扇紧闭的门。两边的人唯一能看到对方的,就是门上的小洞。
这种关系不是天生的。我在四川一个人情味很浓的农村长大。每到过年,村里都要举行长长的“粑粑宴”,招待十里八乡的亲戚,他们肯定会大老远地去赴宴。我跟在表哥后面跑来跑去,去镇上买猴猴,蜘蛛枪,无名鞭炮玩。
12岁后,我离开小镇去省城上寄宿学校,回老家的频率变成了一两年一次。曾经熟悉的长辈渐渐变得陌生。每次回老家,父母的堂兄妹和他们的配偶总会认错,造成很多尴尬。我只是简单的跟着父母,就像鹦鹉一样,他们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如果年纪大了,就躲在车里,一个人做作业,或者抱着电子产品,避开繁文缛节。毕竟亲戚的问题几年不变,我突然觉得他们询问的背后,并不是真的关心,只是在走一个流程。我对父母的作用,只是为了显示“这是我的后代”的功能。
距离隔阂可能是直接原因,但生活轨迹的逐渐背离才是“离婚”的主因。我还在读书,但是大部分堂兄妹都结婚生子了,很少有共同点。
不过我爸妈还是有很强的宗族意识,每年拜年是必不可少的。村里的坝宴,变成镇上的家宴,或者酒店里的酒席。这是家庭权力中心的一次微妙的防御和流转,权力的强弱随着各个小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我小时候,所有的宴会都在德高望重的老人家里举行。后来阿姨家盖了个大房子,很气派,可以放很多桌子。我们在姨妈家聚会的时候,就是强化她们在家庭中话语权的过程。后来我家搬到城里,也请他们到我家聚会,但有些亲戚对权力中心的转移表现出微妙的抵触。
家庭聚会特别强调尊老爱幼,晚辈要向长辈敬酒,说漂亮话。我不擅长这个,更不知道怎么掩饰这个“不擅长”,经常端着杯子尴尬地站在那里。酒席结束,回到家还要被父母指责,被扣上“情商低”的帽子。

来源电影《狗十三》
我的母亲因为一个强硬的理由责备我。她以为如果我不保护这些亲人,以后这方面就没有资源可以利用了。但在我看来,所谓的血缘关系只是我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渠道。我们可以通过雇佣关系解决老一辈需要的所谓帮助。更何况,即使有最亲密的血缘关系,也不代表这种关系会一直亲密。我爷爷去世那年,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妈妈和她唯一的哥哥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我妈会觉得我舅舅没有照顾好我外公,我舅舅会觉得我妈在逃避责任。这些话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双方交流频率的降低,家庭聚会时眼神的回避,让你感觉到空愤怒中有一种情绪。
我不认同父母给我贴上的“情商低”的标签。对他们来说,亲人就是朋友,但对我来说,朋友就是朋友,亲人就更远了。
但是又一次因为过年的酒桌礼仪发生了争执。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也追求真诚的对待,但我们更渴望的是一张平等、实用的桌子。朋友聚会不需要太多的场景,职场上也有新的交流方式,不会因为你在酒桌上什么都做了就对你评价很高。争论到最后,我发现我们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想要灌输的是他们的社交技能。
至于所谓的“离婚”,我更倾向于分开来看。“离婚”的是那些不是我们主观选择的,只是有血缘关系的,而“亲近”的会是那些我们主动选择的“家人”。我们是计划生育时代长大的孩子。不像老一辈有足够多的兄弟姐妹和庞大的家庭,我们还是会爱别人,建立新的人际圈。毕竟,家不再是我唯一的港湾。
我有许多同学和朋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独生子女,但我们的感情很深。在我们之间,我们扮演着家庭一部分的角色,我的“爱”的能力并没有因为我与亲人的疏远而受损。最近在看《欲望都市》,特别羡慕剧中四位女主的友情。剧中有一个情节。当比格先生想去巴黎救嘉莉时,他去参加了女孩子们聚会的早餐会,并对她们说:“你们三个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你们是她一生的挚爱”。

土元电视剧《欲望都市》
我特别认同朋友是我选择的家庭,我们在这种严肃的管理情感中获得了比血缘更重要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方式。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家庭正在瓦解,缩小成越来越小的单位。我们会越来越多地把情感需求锁定在少数直系亲属身上,向外拓展我们新的“家庭”(朋友)圈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和父母有一个博弈,但在这个博弈中,我们会逐渐找到新生代的价值置换和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