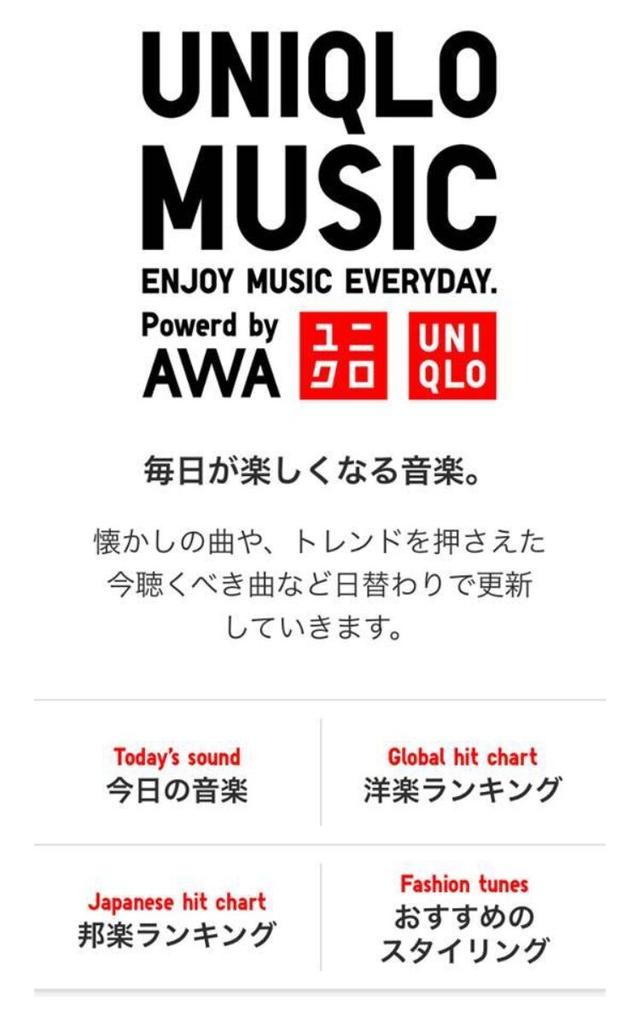随着殖民地教育和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推广,非洲语言出现了大规模拉丁化的潮流。这并非为了使伊斯兰教信徒皈依基督教,而是向他们提供别的语言书写方法,以切断所有与阿拉伯语的联系,进而防止没有伊斯兰信仰的非洲人信奉伊斯兰教。这就是采用拉丁语字母系统书写非洲(尤其是尼日利亚)语言的根本原因。同时,豪萨语字母系统的拉丁语版本——博科(boko)——通过印刷广泛流传。20世纪30年代,这也许是殖民者的策略,但后来这种语言大行其道,则是出于别的原因,尤其是因为标准化。我们还要记住,此时土耳其的语言也正在经历拉丁化的过程。斯瓦希里语也是如此,19世纪末,斯瓦希里语是天主教传教士使用的中介语言,而新教教徒却不太愿意与伊斯兰教展开神学对话。但是,为了挪用非洲语言,这种对话又是必需的,因为斯瓦希里语中很大一部分表示概念的词汇来自阿拉伯语。最终,索马里语(Somali)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拉丁化,并成为前索马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在完成了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字母系统的切换之后,人们开始大规模将以前没有文字的语言书写出来。有些语言由此出现了相当复杂的问题,下文的图标就标明了书写科伊族人(Khoi)语音(如吸气音)的不同方法(see Figure 1.2)。1854年,国际音标的诞生为比较不同的语言提供了有用的对比工具。由于研究者的语言背景不同,这些语言以前是以相当混乱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法国传教士会写出-ch,而英国传教士写的却是-sh:托马斯·莫弗洛(Thomas Mofolo)将祖鲁族英雄的名字写为Chaka(-ch是这个祖鲁语摩擦音的法语拼写),而非Shaka,这种做法是因为他曾虔诚地受教于巴黎派来的传教士们。

推广文字尤其是印刷术,一直都是来到非洲的传教士们的任务。(see Coldham1966)但是,如果不能就文字的拼写达成一定共识,那么每门非洲语言书面形式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生为约鲁巴人的塞缪尔·阿贾伊·克劳瑟主教(Bishop SamuelAjayi Crowther)是语言学家、探险家和翻译家。由于他的开创性工作,约鲁巴人于1875年就拼写问题达成一致(see Ade Ajayi 1960)。这大大推动了约鲁巴人书面文学的发展。宗教差异产生了不同的书写系统,所依据的是各门欧洲语言的规范。有时,民族主义也在发挥作用,而且影响力会持续很久,这从南非和莱索托(Lesotho)对同一门语言塞索托语(Sesotho)的拼写差异(Shaka orChaka)可见一斑。如今,南非索托人巨大的市场如同强大的磁场,未经任何语言会议就转变了莱索托出版商的正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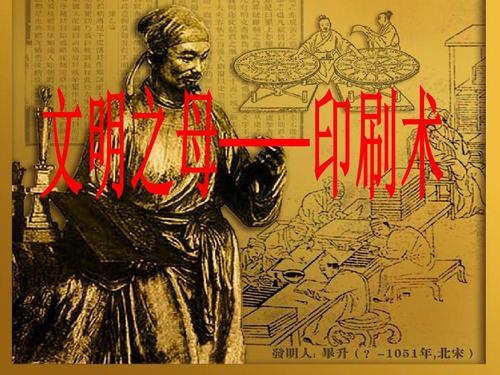
非洲语言的书面化也产生了历史遗留问题,即教会与教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波多诺夫(Porto Novo)——属于贝宁共和国(Benin Republic)——的鹘族人(Gu)书写自己语言的方式,与约鲁巴族(尼日利亚)是很不一样的:分而治之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必要条件,在彼此相通的语言之间创造出不同的书写形式,就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能够分化彼此竞争的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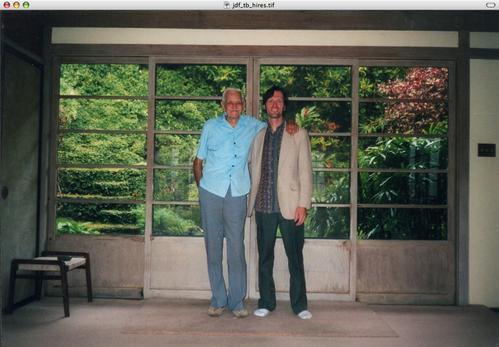

根据典型的浪漫主义世界观,在19世纪,用文字书写一个非洲民族——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意味着将其带向光明,令其走出黑暗时代。世界是根据"分水岭"来划分的:古腾堡(Gutenberg)是"黑暗过去,白天来临";1840年,为纪念活字印刷术发明400周年,在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第二交响曲中,合唱团就是这样唱的。关于图形表达的一般理论不应把字母书写作为人类文化的顶峰,应该拒绝那些颇具民族中心论偏见的著名学说:其他文化走上了别的道路——例如在亚洲和非洲——但这一点常被人遗忘。有关非字母系统的错误观念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例如,有人认为汉字的书写完全与发音无关;相反,这种观念却认为拼音文字能够发展出逻辑思维的能力。对此,约翰·德范克作出了公允的评论:"在解释希腊在思想文化上对于近东邻国(这些国家早于希腊500年就拥有了初步的读写系统)的支配地位时,为什么……只突出这种辅音+元音系统;对这种[Goody and Watt]方法,未见有任何具体分析。"(De Francis 1989:245)这些都是带着东方学残余立场的摩尼教二分法,在有关非洲的研究中尤其盛行,阻碍了研究者将埃及的材料纳入非洲语境。
回到一个包容的视角,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文字史中的非洲篇章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漫长的;对于口头语言——勒鲁瓦·韦尔(Leroy Vail)和兰德格·怀特(Landeg White)所谓的"口头人类的诞生"(1991)——的执念,与其说是论证详实的理论观点,毋宁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