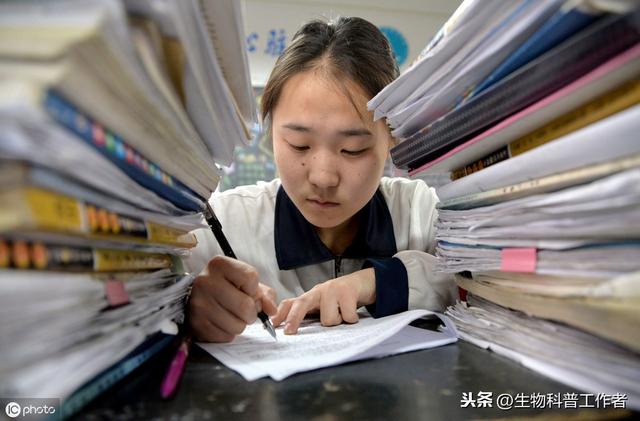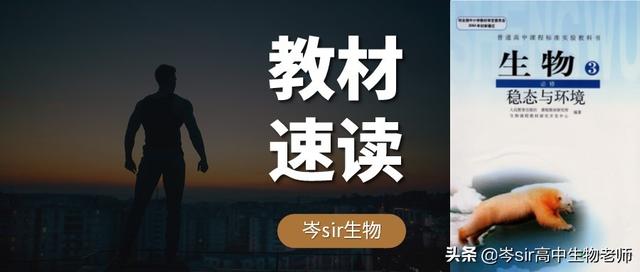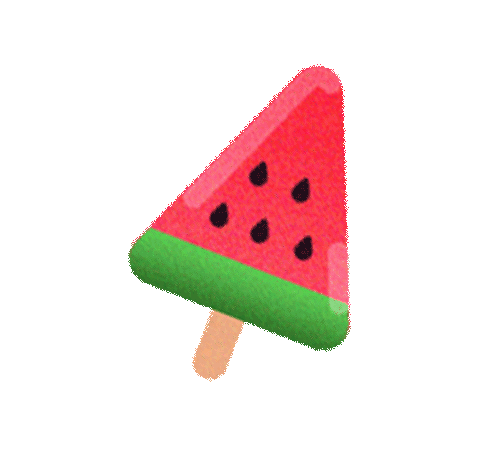说到初唐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初唐四杰”。在“四杰”中,王波被《四库全书总目》提升为“四杰之首”,这也是当年杜甫所认可的。但“四杰”的排名可谓是不同文献中的一个公案。开元初年文学家张国公说王排名第一,而“四杰”之一的杨炯也曾说“以鲁为耻,以王为耻”,可见在大师中,根本不在乎排名和排序,大概是不合理的。“四大宗师”可以算是所有的奇才。明代石庸对《诗镜》的总体评价中,有一句高度凝练的赞美之词,即“高华,杨炯丰盈,邻清藻,王”。他们总体的文学风格,尤其是骈文,可以概括为“思强而主,浩如烟海而盛”。说到他们的运势,都是真的倒霉,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高运萧条的典型。记得30多年前,我去南昌出差,王腾馆是我的首选。1300多年来,王腾馆经历了28次风风雨雨。第29次修复创建于1983年,于1989年重阳节完成。我参观了王腾馆,不久后又到了登思楼,远眺水天一色的赣江,不禁吟诵起王波《王腾馆序》(别名《秋登鸿福·王腾馆别》)中的名句。这是一篇文笔优雅、才华横溢的文章,流传千古,但围绕这篇文章一直争议不断。一个争议:这篇文章是王波什么时候写的?众所周知,王波只活了27岁,不是因为他病死,也不是因为他战死沙场,而是因为他淹死了。就因为他会长生不老,争议空很压缩。只有两种意见:一种是14岁写的,一种是26岁写的。现在1000多年过去了,决定了吗?很遗憾的告诉你,没有!在14岁的作家(以下简称“14岁学校”)上,王波于663年春天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旅行。他在江苏六合拜访时任县令的父亲王夫之,渡江访绍后,一路回江西到南昌,应邀参观王腾馆,并为王腾馆作序。明代杨慎曾说:“王波是十四岁少年,胸中有万卷书。时隔千年,秀才仍不知其源。”在26岁的作家(以下简称“26岁派”)身上,王波的事业在他弱冠之际受挫,从此做好了吃苦的准备。26岁去交趾省路过南昌,才有了这种感觉,写出了这部巨著。穿插这两个不同年代的写作渊源,即王波是14岁去南昌还是26岁去南昌,都涉及到洪州总督(即开篇第二句中的“洪都新居”)龚燕。路过此地的王波也应邀参加了某年9月9日为庆祝王腾馆修缮竣工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在那天的庆典上,故意让他的女婿吴这个很有文采的人展示他的本事,所以他提前为亭作了序。为了显示“正义”,设计了一个礼节性的环节,或者说是采用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形式,即给每位来宾赠送一支笔、墨水、纸张和砚台,作为王腾馆落成的前奏。

天空充满了色彩,现在是日落时间。
当大家都知道“礼仪”是谦让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的王波居然拿起纸笔,然后用墨水写了起来。龚燕很生气(太忘恩负义了)就走了(在隔壁的帐下),但为了还“文”却派人留在了现场。可想而知,在一个特殊的人和人群的注视下,仍能思绪万千,临场发挥的王波,有着极佳的心理素质和惊人的文采。当王波的第一句话“南昌老县城,洪都新居”来的时候,严正义大师正在生闷气。听到这里,龚燕突然轻松了一点,脱口而出“也是老生常谈”,而刚才对修养的一点生气,似乎也变成了“等你出丑”的期待。在第二个报告中,云说,“星星分成翅膀,地面与鲁恒相连”。龚燕一听,应该是心里咯噔一下(或者他识货),却一时语塞。后来,当报道“夕阳与寂寞的齐飞,秋水同色”时,龚燕终于坐不住了。突然,他说:“这是天才,而且是不朽的!”所以我热切地邀请宴会,并且非常高兴地离开。龚燕虽然头脑不够清醒,但并不糊涂。他很清楚,他的女婿在文学才华上远远落后于王波。如果他仍然僵持不下,他会害怕招致舆论,而干脆赞美王波并大方地摆酒。难道他不会表现出识人爱才的胸怀吗?这个故事的起源是王编的《唐集》。虽然不能将其视为史实,但唐代诗人、学者的大量轶事,在弥补正史空白和未知方面,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另外我参考一下袁心文的《唐才子传》(第一卷第三章),关于这件事也有一句话:“要聪明,要帅,要知才,因为请做。”鲍勃很高兴与客人交谈,一瞬间,他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他充满了惊喜...”,但语气凝练平淡,不像唐那样“添油加醋”。说实话,我很理解“十四岁派”的观点。王波“六岁即识字,立意不滞,词中英格拉姆微”(《旧唐书传》);”九岁时,我读了颜氏的《汉书》,写了十卷《指瑕》10岁集六经,成了一个月”(杨炯《王子安集序》),12岁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师从长安名医、术士曹渊,学习了《黄帝苏文》、《周易张炬》、《难经》等。经过十个月的学习,我“得偿所愿”。所以,文采出众,熟读经史,才华横溢的王粲伯,怎么会在14岁就写不出《王腾亭序》呢?此外,赞美“龙驹凤雏”这样的神童一直是民间传说中的一种常见嗜好。但我的阅读还是偏向于“26岁派”。为什么?因为生活的历练和苦难的磨炼并不是所谓天才神童所具备的,结合《王腾亭序》中那些阴郁阴郁的歌曲,似乎并不出自一个14岁少年之口。这就不能不提到一生中的一个重大打击:17岁就收了鲁,当时他正在(即太子)手下“写作”,颇得的喜爱。然而,这位天才的职业生涯因为一场斗鸡和一个无足轻重的“王赢·文姬”而戛然而止。当时宫廷里流行斗鸡,国王都玩得不亦乐乎。有一次,沛王李习安和郢王李哲斗鸡。为了讨裴王欢心,王波根据调侃写成了《迎凤王》。李习安反应如此之快,以至于他派人将这篇骈文像挑战书一样提交给李哲,这导致了宫殿争相复制和传播它。不想这一条落到皇帝手里,皇帝大怒,认为有“渐变”之嫌,下令免去当时年仅20岁的王波一切官职,立即踢出裴,永不录用。整件事是由王波对世界的无知造成的,也与唐朝建立后君王间勾心斗角的政治阴影有关。作为父亲,皇帝李治经历过这么血腥的事情,所以神经有点过敏。在读了王波那篇无害的文章后,他认为那是在挑拨王子之间的家庭关系。盛怒之下,他出手太狠,将羽翼未丰的王波置于人生低谷。

在歌舞的点缀下,王腾馆的夜景越来越丰富多彩。
然而,仕途的沉沦构成了王波文学人生的重要分水岭,是所谓“苦难出诗人”的又一典型。在被培开除之前,王波的作品多以书、悟、表、赞等形式写成,充满才气但分量不够。被裴开除后,他的作品越来越丰富,大多抒发了思乡之情和乡愁,感叹世态炎凉,抒发了内心的委屈,表达了人生的抱负。所以,在《王腾亭序》中,我们就听到了这样一句人生感悟:“喜来悲往,知识丰足。阳光下看长安,云里看武辉...山难跨,谁为迷路的人难过?萍水相逢,都是外地客人.....太巧了!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如果14岁的王波就能写出如此苍凉深沉的文字,是不是太早熟了?这也是我认同“26岁派”的根本原因。再来说说《王腾馆序》中的另一个数字争议。其实和之前的争议有着必然的联系。紧接着引文的是《王腾亭序》中的另一行的第一句话,这是这场争论的由来:“伯,人生三尺,秀才。“据《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和《中国古代文学珍品》的记载,说‘历代文学成就赫赫有名,三尺少言’,可谓含糊其辞。民国学者高步英和当代学者王力把“三尺”称为士绅带(下层官僚腰带平衡下垂的长度),也有人认为“三尺”是指他们的身高,以证明文章确实是14岁写的。这就涉及到“一尺”的测量标准,但历代并不一致。结合中国国家计量总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显示,在商代,一尺约为今天的17厘米(以下所指的“厘米”均为17厘米左右)。按照这个尺度,男性的身高在一尺左右,这就是“老公”一词的由来。如《孟子·滕文公子》中有“效法徐子之道,则市场价同,国无虚妄;虽然都说五尺小儿适市,不可欺,但从战国到汉代,一尺相当于23厘米。如果按照原来的“人生三尺”来衡量,14岁的王波身高太矮了。在王波生活的唐朝,一尺的概念是30厘米,三尺的概念只有90厘米,与14岁孩子的正常身高严重不符。有一次,我偶然看了一本关于日本正仓研究所(日本奈良的一个仓库)的记录,研究了相关论文。据说正仓院有一卷年号为“庆云四年”(707)的《王波诗序》,这意味着它是王波去世后大约30年的产物。但令人惊讶的是,根据它的原始记录,并不是“鲍勃,三尺微命”,而是“鲍勃,五尺微命”,这不是微小的差别,而是将近70%的差别。考虑到《正仓院》是王的原始文集,史料价值和可靠性不言而喻。《三尺》的版本有错吗?日本学者道坂昭弘认为“三”可能是当年抄写时的笔误,这也是它给后人带来误解的原因。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14岁派”将得到更强的支持,因为如果王波的身高突然“飙升”到150 cm,将更符合14岁这个具体年龄。然而,道坂赵广的观点并不确凿。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假设,即“五尺”也可能是作为后进生的王波谦虚地称自己学术能力不足的一种措辞(这种说法也很难确定);至于其他一些论点,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只好在这里“搁置”争议。事实上,无论《王腾亭序》是王波14岁还是26岁写的,无论原文是“三尺微命”还是“五尺微命”,作为传世的经典骈文,其一流散文是举世公认的。每次看这篇文章,或者在历代书上写这篇文章的法帖,都能感受到一种“飞如电击”(陶渊明《杂诗十二首》)的气势。俗话说,追不到过去。新人怎么继续?在研究了王波的一生之后,就他的成就而言,他确实没有表现出他的野心。但就文学成就而言,不说别的,仅《王腾亭序》一篇就足以流传后世。这是欧阳修所说的“君子之学,或其业,或其文”的内在含义吗?

本文图片来源:新华社
主编:黄炜文字编辑:吴斌
来源:作者: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