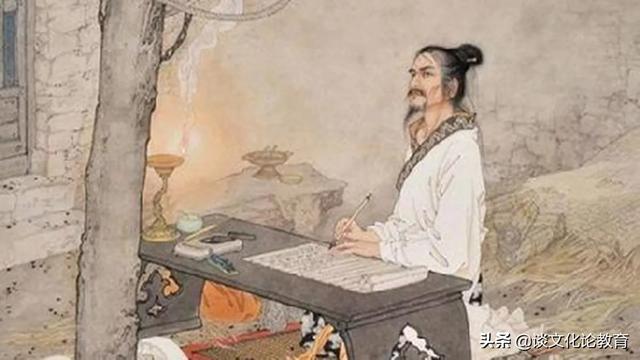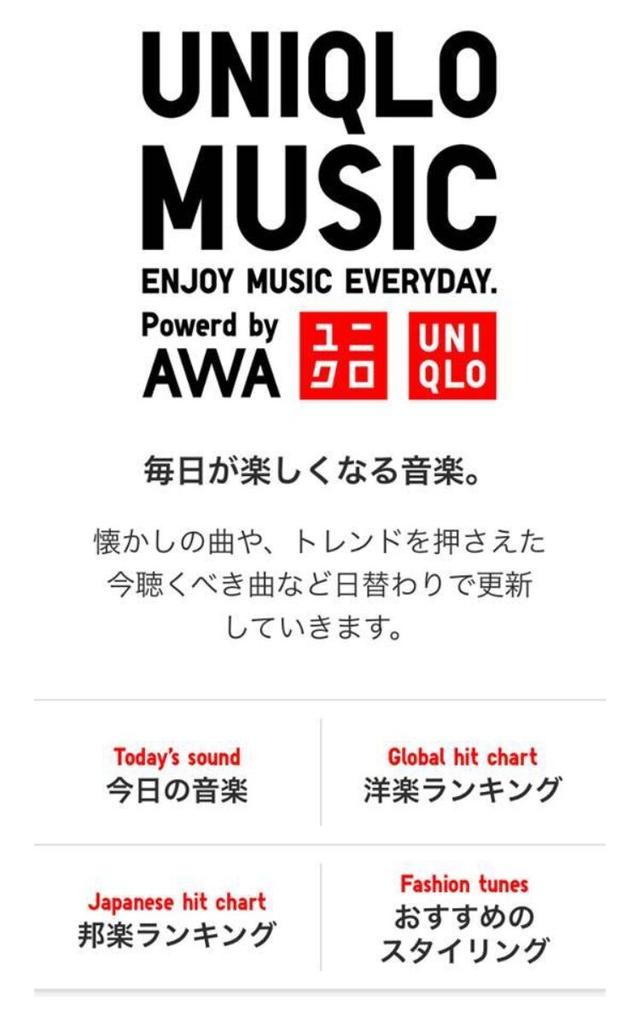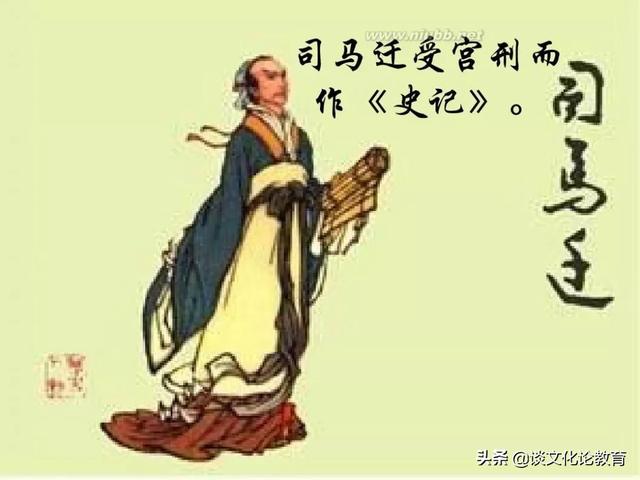
《史记》是中国古典文史名著,一部国学精品根柢书,可以说应该是人人必读之书。20世纪初,倡导新史学的思想大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史记》,他曾走上讲堂向学生们宣讲《史记》,并倡言大学讲堂应有《史记》的一席之地。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开设“中国历史名著选讲”,即后来的《中国历史文选》课。
《史记》成为陈垣先生的一部重要的讲读书。《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先生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精品中,《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历代无数文史大家,无不得益于《史记》的养育,得益于司马迁精神的鼓舞,对《史记》长盛不衰的研读热情,使司马迁的精神得以永存。鲁迅先生称她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司马迁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千载之下更是令人羡慕不已。”
司马迁是以一种广泛涉猎和考证的求实精神,采集到历史生活中的真实,从而纠正了史料中许多不实之处。这些记载充分表现出司马迁丰厚的学识和社会实践之深入,又增强了《史记》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禹治水”,这一历史真实,一直被今人当作古之传说而变得虚无,直到2002年保利集团从香港购回青铜器《豳公盨》,上面铸有“天命禹敷土”之铭文,且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人们记忆中大禹治水的传说才成为更加确凿的历史事实,而得到学术界的一致承认,也使《史记》中“五帝本纪”中鳏之一脉延续至“禹”之夏代得到证实。
结合《豳公盨》,《史记·夏本纪》中早有:“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以決九州致四海,浚畎澮到之川”。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帝命禹敷理全国土地,禹便带领百姓徒步行走在高山大川,顺着山势,在树上作标识,疏浚河道。“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禹谓帝舜曰:“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禹在外治水十三年,路过自家也未敢进去看一眼,而对治水的百姓却亲自把食物分配给他们,结果百姓安定,国家也在大洪水之后得到治理。
《史记》中也有禹与帝舜的一段对话。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而止。辅德,天下大应。”帝舜曰:“吁,臣哉,臣哉,臣作股肱耳目。予左右有民,汝辅之。”
这段对话又恰恰说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成为帝舜的股肱之臣,辅佐帝舜推行德治,得到天下应和。而这段话的关键词或者说中心意思“德治”“辅德”又在《豳公盨》铭文中得以契合,如监德、唯德、明德、懿德、好德和兹德亡悔。由此,也证实了陈直先生曾经说过的:“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之不谬。
再有,《史记》中《秦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始皇陵被项羽率兵所焚毁,历代皆传,然考古工作者自1962年至近一直对秦始皇陵附属陵园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考古探掘发现,秦始皇地宫两千多年来一直安然无恙,不仅穿三泉,椁周铸有青铜护壁,而且地宫中充斥水银气体,通过卫星探测,地宫中溢出的水银气体高于周围地区。
最终证实,项羽当年率兵并未进入皇陵地宫,而是焚毁了始皇陵(陵塚)周遭的九层之台及护廊和陵塚顶部的享堂,其中也包括已发掘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等附属陪葬坑。所以,专家得出结论,《史记》记载无误,倒是《汉书》记载有误。
由上述几组实例证明,司马迁著《史记》并非道听途说,也非信口而言,而是经过缜密的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的认真筛取,尽最大努力记述历史,还原历史,再现历史,以期把人们带入特定的历史时空,让人们直观,感性地触摸历史,体验历史,记住历史并传承真正的历史。

《史记》为二十五史之首,内容及其丰富,她是一部融史学、文学、哲学於一炉的旷世大典。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一向为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镇。

人们把《史记》称为是一部雄视千古的杰作,称赞司马迁忍辱负重,拼死著史的气魄和大无畏精神。为后人记录下卓越的史实和充实的内容,以及书中体载的构建,体例的运用和叙事的才华,不仅使《史记》成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成为传记文学之名著。
通过《史记》,司马迁实现了自己定下的三项著史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史学,她的特点是体大思精。体大,是指《史记》的五体结构规模宏大,体系完整,是一个系统工程;思精,是指《史记》内容丰富,囊括中外,贯通古今。她上起黄帝,下讫汉武,汇总古今典籍,“网络天下放矢旧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通史。
由于《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遂成为传记文学的典范。有人说《史记》蕴涵着进步的道德伦理思想,开明的政治治国思想,富国利民的经济思想,民族一统的和谐思想等等,是一部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的道德伦理书。
认真学习阅读《史记》,还让我们认识了司马迁,了解了祖国优秀文化历史的演进脉络和为民族建功立业的那些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认识到中华民族发展至今之不易,以至要更加明白珍惜先贤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之珍贵和不可多得,所以,真正让我们从司马迁著《史记》中读到的不是失败的挽歌,也不是悲伤的叹息,而是大无畏的进取,是胜利成功后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
因为在那个崇尚英雄、追求功名的时代,人只有为理想,为民族、为国家的利益献出生命才重于泰山。因此,司马迁在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严酷抉择之中,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道出了震撼千古的至理明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也的确迸发出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理想者澎湃的心声。司马迁的经历,正是古今中外思想者人生历程的缩影。
我们说《史记》的精髓就在于她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结束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笃实,自强不息的精神,她澎湃着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激情,她像黄钟大吕一样迸发出一种阳刚之美,她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传奇,是华夏几千年的英雄史诗。
这种文化精神不仅体现在历代王朝的承敞易变上,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历史行为之高度。在平治天下的过程中,士林阶层的形成以及与天地相参的人生价值观所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核心,就成为了我们伟大民族生生不已的文化灵魂。
从《史记》中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太史公是一位具有伟大的气魄、深刻的眼光、丰富的生命体验和大无畏胸怀的真正史家,他“不虚美”,“不隐恶”,经受了至深的苦艰,然而,他却没有泯灭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与历史进取心,相反,他变得更加英勇。他高扬起生命的意志之帜,以忘我的精神沉浸于记史传史的伟大事业之中,最终以他自己全部的生命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永恒,让后人永远铭记在心,成为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
任何一个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政治学说时,都要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现实需要去吸取前人的成果经验,而史书则是要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真实准确的叙述,总结历史经验,使无论哪一个方面的读者都能从其叙述中了解过去,从中受到启迪,更清楚地认识现在。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无疑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对《史记》记史的真实可靠应该敬畏与深研不要轻易否定《史记》中的历史内容。今天社会上有一种议论,认为《史记》中的一些记载是司马迁采撷的传说故事,未必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史实。
对《史记》记述史实的真实性、可靠性,一直持尊重和不轻易否定的态度和立场。因为司马迁毕竟比我们离那个时代要早两千多年。许多事情的发生,它的社会环境,人们行为做事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出入极大。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当年古人未必敢作敢为,而古人当年的所作所为也远非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复杂。所以,我对社会上对《史记》的各种议论更不敢苟同。在这里仅举上个世纪发生的两件事也许对我们理解司马迁写《史记》会有帮助。
一件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动乱”,这件事仅仅过去三十几年,其中的许多人和事,让今人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成了被人遗忘的历史,甚至没经过这场动乱的年轻人更认为那是前人编造的故事,打死也不信。“十年动乱”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身边的事,而这一代人又对几十年前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不甚了解。
说起那场运动也不那么感觉深刻,单从文字上看是平面的。相反,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对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却刻骨铭心,是立体的,每每提起都让亲历者不寒而栗。例如傅雷等一大批优秀爱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竟决定了一个家庭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让人闻之扼腕。
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一代人都对历史的认识有自身的局限性,继而,对司马迁写《史记》的认识和判断也不可以认为其中记述历史史实有误或认为其中的文字有夸大之嫌,只要我们认真阅读《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记述历史史实的认真严肃简直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然从记述史实的文字角度看,司马迁语言文字和文化修养之高古和纯熟及叙事编排之鲜明深刻都是空前绝后的。作为今人对此只有敬畏和深研,而无资格妄加指摘。
现在引用两位前人的话,看他们对《史记》的认同和认可,也许比我们更贴切更深邃。
一位是北宋的苏辙,他从文的方面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另一位是清代的顾炎武,他从武的方面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当代学者陈直先生则是用考古发掘与史书相对照之两重证据法证明司马迁写《史记》之经典。他在其著作《史记新证·自序》中说:“太史公作《殷本纪》,合于殷墟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如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頵,皆与传世铜器铭文相符合,尤见记载之正确性。又如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即无从参考。更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所记立大市、立谷口邑,立阳陵邑等,皆不见于《汉书》。反与出土古物,若合符节。”
出土文献印证《史记》记史的深度与广度出土文献证实了《史记》记史的可信性。而《史记》真实的记述又为后人研究出土文献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从历史学角度讲,《史记》的“实录”也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