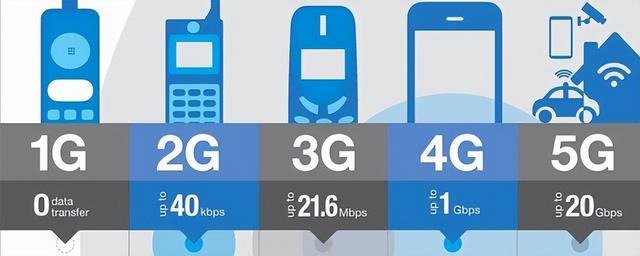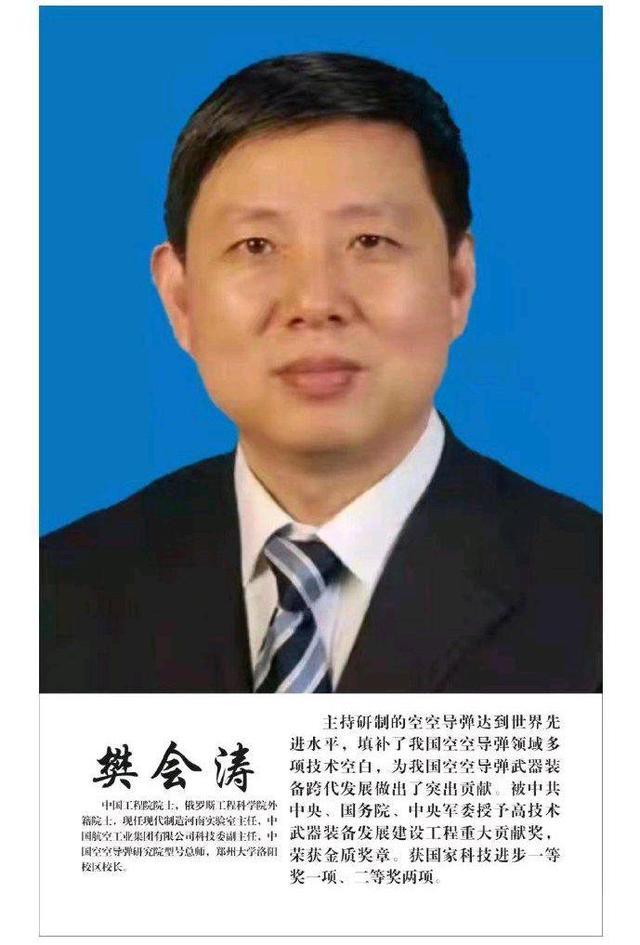鲁迅孙子周令飞
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孙子周令飞却意外“走红”。事情的起因是,周令飞多年前回忆往事的言辞被人们翻出来当成“段子”疯传。“段子”的梗概是:周令飞走到哪都被强调是“鲁迅的孙子”,这个身份让他如芒刺背,为此只能怀着恐惧和压力逃离本来的生活。然而让周令飞困惑的是,自己年少时去当兵,别人告诉他鲁迅是弃医从文,他就需要继续祖父未完成的事业,所以被安排到卫生所。后来周令飞又被安排当通讯员写文章,但他不喜欢写作,别人却不信,说鲁迅的孙子怎么可能不写作,他实在写不出来,排长递来一根烟,周令飞说不会抽烟,排长说鲁迅都抽烟,你为什么不抽烟。一言以蔽之,周令飞不仅无法回避“很像”鲁迅的事实,也无法逃离被鲁迅人格绑定的局面。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无论是“段子”本身的叙事,还是“段子”让周令飞“走红”的叙事,都透着很浓的“反讽”氛围。要知道对于“段子”本身的叙事来讲,属于世俗考量中典型的刻板印象。换言之,就因为鲁迅是名人,就好像他的后代必须延续他的一切(社会人格、人生选择、生活方式等等。)可事实上,这又怎么可能呢?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否认“家传技艺”的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必须继承先祖的衣钵。尤其对于鲁迅来讲,他的人生经历也好,个人影响力也罢,就算周令飞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过一遍,并且在既定的轨迹上都做到业内顶级,但也未必能探到鲁迅之于社会的影响力,起码就人们的惯性思维来讲,周令飞永远无法超越鲁迅。
至于“段子”让周令飞“走红”的叙事,这显然是“亚文化”之于世俗考量的对抗,并且也是之于鲁迅思想层面的某种实践。说到底在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如果真要有所表示,那最好的纪念就是思想层面的突破,实践层面的反思。就此而言,与其说周令飞是意外“走红”,不如说是人们通过制造他的“走红”在批判世俗考量。
而对于周令飞回应“做名人后代难”这个插曲,其实更多的考量之于他的主观感受,并且是趋向精神层面的难耐。因为就现实的考量来讲,好的家庭背景对一个人极其重要,这使得相较“做穷人后代难”,所谓“做名人后代难”简直可称得上是“凡尔赛”。
当然周令飞的感受只有他自己更清楚,而回到鲁迅孙子的叙事里,人们在看待周令飞的存在更多是以“平面鲁迅”(文本印象)涉入的,而非是“立体鲁迅”(整体印象)的涉入。这使得周令飞很容易被人们工具化,也就是成为陈设“平面鲁迅”的架子,而非是以爷孙关系去认识周令飞,去体味鲁迅。

所以要承认周令飞的“走红”还是之于鲁迅影响力的延伸。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看待鲁迅的影响力是一回事儿,如何看待周令飞视角下的爷孙关系是另一回事儿。只有将两个层面的关系掰扯开,才可以更好的理解周令飞的感慨。
就鲁迅的影响力而言,它本身是历史级别的,所以更显的平面化,也就是基于文本在画像鲁迅。这种情况下,鲁迅作为周令飞爷爷的印象就会被严重折叠。当然客观来讲,作为众多的读者,也没必要悉数了解鲁迅作为周令飞爷爷的印象,但是回到具体的审视上,还是要回到人本身。
严格来讲两个层面并不矛盾,只是人们在具体涉入的过程中总是会走向偏狭。尤其在“段子”中呈现出的逻辑,显然把鲁迅的孙子彻底印象化,也就是基于鲁迅印象来认识周令飞是谁,他会做什么,他该干什么。而非是直接的去认识周令飞是谁,他能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另外从周令飞感慨“做名人后代难”的逻辑里,我们也可清算一下世俗考量中刻板印象对人们的困扰。因为对于“做某某某某难”这个语词模版来讲,可应用的场景实在太多。典型的如“做富人妻子难”,可做穷人妻子容易吗;“做帅哥女友难”,可做丑男女友容易吗;“做美女老公难”,可做丑女老公容易吗。如此种种,“做某某某某难”只是相对表达而言,回到公论上真的意义不大。
这样的前提如果成立,那么对于周令飞感慨“做名人后代难”的表达,也只是就社会偏狭而做出的感慨,并不是说他觉得当鲁迅的后代真的痛苦难耐。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分,否则容易被只言片语带偏。
要承认人格出现在公共领域,本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出现了世俗观的结果。这种世俗观通过对具体对象的解释或标定来取代对象本身及其延伸部分。所以就刻板印象来讲,如果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想要打破确实也是很不容易。
与此同时,借着周令飞和鲁迅的社会影响力差异,也可审视家庭教育中存在的既定偏见。普遍来讲,家长都希望孩子比自己有出息,在这个预设的前提里,如果家长已经在既定的圈层里很有影响力,那么在期待孩子的预设上,不如把“比自己有出息”换成“走自己的路”更好。
当然这里所言的“走自己的路”并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孩子只要能生活的好,并拥有自己的热爱,那么家长不妨把期待降低为好。毕竟要是较早的把期待前置,会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压抑,起码会形成很重的内耗。
实际上社会中的各种偏见已经让孩子们很难受,如果在既定的家庭环境中依然没有宽松的氛围,那么作为个体的人确实会不由得发出“做某某某某难”的感慨。 循此而言,周令飞的感慨何尝不是对现实的揭示,冥冥之中也算是对鲁迅思想的实践,而非只是“亚文化”消费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