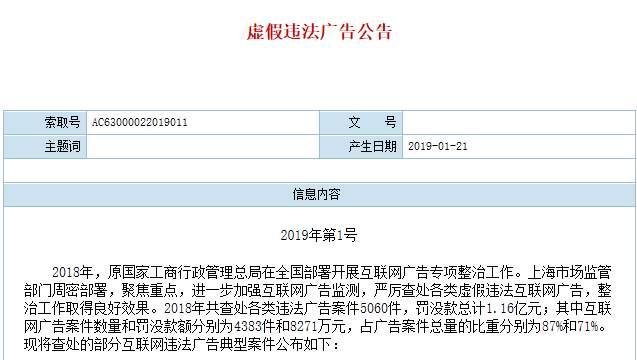下雨的下午。我很难确切地说出这场雨下了多久,似乎有好几天了吧。成都的雨不像故乡的雨,不停地下,把大地浸润透了,方才停歇。成都,它不,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间或还出一阵太阳。所以,成都的气候,更像一位官宦之家的大家闺秀,温柔和脾气共存,感性与理性同在,总之,感性大于理性,因为,它不太顾忌大地的感受。
下午的时光,下午茶闪亮登场。一本书,一壶茶,这才是读书人闲暇的标配。
酒,使人亢奋。而茶,却使人慵懒。四点钟,过了下午茶的时间,文字泡在茶里,人掉进了文字,想起晚餐,柴米油盐,便一地鸡毛。不想动啊!
我向来对穿着和吃饭是不马虎,今天却想马虎一下,蒸一个咸鸭蛋,切几片咸榨菜,再煮一盅玉米糊,晚餐便能对付。
没成想玉米糊却被我煮糊了。焦糊味充斥着这个略显逼仄的租住屋,久久不能从门窗散去。其实,焦糊味是越来越浓的,我却陷入黑色的文字里不能自拔。
“原来在不停来往的,是这种关乎性灵的时间,它凌驾于我们的肉体日甚一日的衰败之上,直接左右着我们的记忆,超越苦难现世,也超越自然时间的必然律令,从而指向那无垠的大全和终极关怀。”
我当然不能抱怨这段文字,再说了,文字一旦铺陈在纸张上,它的使命完成了一半,抱怨文字无济于事。当文字从纸张上走出来,开口表达,那便是神谕,一种对苦痛身体的救赎。
我也不愿意抱怨自己。物质不灭,把糊了的玉米糊倒掉,还可以再煮。文字一旦走进自己心中的舞台,它是不可逆的,无法返场。
俄国诗人蒲宁在他的《寒秋》中,确实有这样的独白:
“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而其余的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
诗人所说的“他”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也可以理解为记忆中的时间。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值得我们去回忆和回味。

上午,有位友人说:“其实我经常挺抑郁的。”我说他是阳光型抑郁。他说:“我经常觉得自己在一个沙丁鱼罐头里。我的工作不能给我带来成就感和活力,而韶华飞速流逝,我一事无成。”我告诉他,人处在黑暗之中时,往往忘记了自己也能发光。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发光体。
发光可以让人活得更多,即使不是活得更长。长,只是一条流线;而多,则是立体的,丰盈的。
就在刚才,北京的友人汤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老朋友好!粗略拜读了三部大作。虽然未及仔细品味,已然收获了很多精神营养。近几年,你那么坎坷,我竟不甚了了,有失朋友之责啊。大难挺过,必有后福。你这一发而不可收拾地推出系列作品,便是明证。期待新作……”我回:“嗨,我不觉得有什么坎坷。任何所谓的坏事,把它当好事接受,它便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