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猫4982亿,JD.COM 2715亿,双双创双十一购物节新高。在被疫情和经济衰退围困的一年里,这些全民创造的数字,似乎可以掩盖很多恐慌时刻。比如创纪录的时候,多少人借的钱多?
一周前,蚂蚁金服的“全球最大IPO”计划戛然而止,引发了一些关于年轻人借贷消费现象的讨论。但双十一的“战绩”证明,这些讨论并没有真正引起消费群体的警惕。
趁着购物季,我们采访了三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在一线城市工作,有或正在背负贷款。他们的债务历史和额度可能没有昨天微博热搜发帖的豆瓣集团债务人联盟成员那么震撼,但可能更有代表性。
事实是,这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避免负债的时代。在这个消费和借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方便的时刻,不使用信用卡和各种消费信贷产品的人就更奇怪了。只要你能搪塞自己的现状,任何慌乱的时刻都不会暴露。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借贷更多时候更像是一个小问题。
一个
“柏华的还款日从9号开始,后来我把它挪到了20号。白的还款日是6号,分期乐是19号,是8号……”青子说不清欠了多少钱,但她能记得各个借贷平台的还款日期。第一次计算时,她的负债总额为5万元,第二次计算时,这个数字似乎更接近7万元。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绿孩子人生的危机。在P2P雷霆事件频发的这些年里,生活中暴力催收、家庭破坏的轶事比比皆是。青子的债务都是向“正规”平台借的,即使她从不记账,她也知道自己每天的开销无非就是吃饭打车,更不用说为赌博吸毒之类的严重问题买单了,更不用说去哪一个能出现在社交新闻页面的时刻了。
此外,吕子在北京还有“过得去”的固定收入。相对于豆瓣知乎上很多负债累累,月入5000,却欠下几十万的陌生网友的情况,不管是5万还是7万,现在的收入让吕子觉得自己的债务有了尽头。而且最重要的是,“欠钱不是小事,信用卡太普遍了,很多朋友为了光鲜的外表还欠了十几万”。
所以,即使知道自己负债五万多,青子也不着急。至少不用着急列出收支计划,关注每个月的开销。“我的计划怎么办?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要人活着,你不就要按时踏实的还钱吗?我心里有这样的意识。”

电影《弗朗西斯·哈》剧照
在北京工作近七年,最多负债八万元的Abby也有类似的感受。她的密友都没有存款,负债最多的时期也是她月收入最高的日子。她已经经历了贷款转贷款阶段。当拆东墙补西墙的周转不灵时,她向朋友借了一些。朋友都很善解人意,最经常互相帮助的朋友,“她赚的比我多,欠的比我多”。
张三刚在北京工作半年就欠了近7万元,具体多少她也说不清。她只觉得当初借钱是临时应急,临时支出三四千元。当债务因突发事件累积到2万元左右时,她也有过恐慌,但分期还款只有几百元,以当时的收入来看还是可以忍受的。
现在回想起来,张三觉得触手可及的贷款让她“不觉得自己没钱,也不觉得自己在花别人的钱”。当白花的钱用完了,她开通了网商贷款,暂时的困境顿时明朗。“看到网商6万块钱的消费金额,我觉得很放心,我会觉得没事。我还有这钱花”。

2019年,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发布消费信贷现状报告,聚焦中国90后或90后年轻人。根据这份报告,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总信用产品的渗透率为86.6%,扣除仅使用其支付功能(仅使用消费信贷,当月还清,不计利息)的约一半后,仍有约44.5%的年轻人存在实质性债务。
II
当天,豆瓣债务人联盟团队登上微博热搜。这个团体成立于去年12月,目前有超过17000名成员。求助的人很多都负债20多万,有的已经破百万了。欠债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对名牌包包、手表等奢侈品的沉迷,到因诈骗、赌博或创业失败而深陷泥潭。大多数人都处于濒临崩溃、难以为继的生活状态。网友们纷纷表示很恐怖。
相对于债务人联盟略显极端的案例,张三、艾比、青子的债务总额就不会那么夸张了。同时,他们不追求奢侈品,也没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总负债在一些看似正常的消费行为中悄然增加。这种沉默是微妙的。一方面不会失控,变得不可持续。另一方面,这种费力的平衡,以及对个人消费习惯缓慢而持续的根本性改变,使得“节欲成本”越来越高。
这可能也是发生在大多数年轻人身上的借贷常态:债务故事通常不是由一个偶然的、低概率的事件或者一个严重的坏习惯开始的。事情首先会从周转不灵开始改变。借贷的链条往往会因为限额而中断,向朋友借钱的次数开始增多。工资和其他收入一有了,几乎都要还给信用卡或者其他借贷平台。储蓄卡里几乎没有钱,日常生活开销都会靠“借”来维持。

电影《一百块钱的爱情》剧照
艾比回忆说,她第一次申请信用卡是因为毕业出国旅游。当时她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出门,但是信用卡还留着。一开始限额只有8000,但是去年,这张信用卡的限额超过了8万。
2015年左右我主动办了第二张信用卡。因为对微集成感兴趣,做了几个项目,花了一万左右。雅碧用信用卡付款。她不认为这是无法支付的费用。她以为那是两个月的工资,几个月就能还清。
这也是艾比工作的第二年,经济形势在互联网的神话中方兴未艾。她刚毕业的时候月薪不到5000,后来逐渐增加。2017年后,她的月薪翻了三倍。2015年微消费后,她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报了外语班,还安排了健身房。她还养了一只猫,每年为自己计划一次旅行。
当年,她对自己的还款能力很有信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心逐渐被收入到手就“消失”的疲惫所消磨。最疲惫的阶段,她知道自己欠了四张信用卡,但不清楚具体的总额。“大概是8万,肯定不止8万。这里不敢加,怕把自己吓死。”

电影《过春天》剧照
张三在2019年6月设定了她贷款额度快速扩张的起点。当时她想申请出国留学项目,需要有人做文书工作。因为不想找父母要钱,她选择了网贷,为了自己多用,比文件原价多拿了一千。后来的旅游和租房费用都是陆续从他们那里支付的,她的宠物也是在这期间不小心被猫传了过去。到2019年底,在她人生或人生阶段发生巨变的半年时间里,她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欠了7万元。
同样,7万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之所以要算出一个大概的总额,是因为她“计划中”的借贷平台突然掉了额度,这样就给她留下了一个缺口来支撑她的贷款,她一时找不到别的平台来封住缺口。
从那天晚上开始,张三就开始计算自己欠了多少钱,需要多久才能把钱还上。“我意识到我不想再借钱了,但我当时没算很久。我需要多长时间来偿还这笔钱?”
三
在知乎、微博、豆瓣上的公开话题和讨论组里,有债务问题的网友都在主动公开自己的债务金额、债务平台、收入水平,最终目的是“上岸”(还清所有债务),但往往被越来越多的催债电话、越来越高的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来。
除了鼓励,其他网友会根据自己的借贷经验给予实际指导。比如如何投诉暴力催收,如何与平台协商降低利息或者只还本金。根据具体的个人收入和借贷平台规定,不同的协商和还款方式会有所不同。
但大部分网友提到的第一步,是向父母家人坦白债务。
对于家里有积蓄的人来说,在欠款数额不大的初期,家里或许可以一次性还清债务,以减少利息,防止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对于没有还款能力的家庭来说,向父母和家人告白,也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救赎”。通过面对亲人的失望,你可以释放自己贷款的压力,不再逃避真实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这是今天很多债务人真正的“成年礼”。
无论家庭贫富,“向父母坦白”几乎是欠债人上岸的第一条戒律。但这件事的难点,或者说悖论,在于很多债务人借钱的根本原因是家庭关系比较紧张。

小鸟女士电影剧照
张三决定不再网贷借钱后,每个月只留500元生活费,其余收入用于还款。所以到年底,她还有近5万的债务要还。她粗略算了一下下线业务贷款的利息,每年约有1万笔贷款要支付1500多左右的利息。她决定先想办法还本金。她告诉妈妈,她有2万的债务要还,希望她能“支持”1万。可是张三的妈妈说她没有钱,让她不要告诉爸爸。
其实,跟父亲说自己欠债的事,根本不是张三的选项。她知道一旦开口,父亲肯定会拿钱出来帮她还债,“但那样他会对我更加不满”。张三毕业后,因为就业选择的问题,和家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她父亲想让她去南方某城市的国企工作,但她还有别的事情要探索和尝试。
张三并不怎么讨厌那个南方城市,但一旦遵从了父亲的安排,似乎以后就要生活在父亲的控制之下,从如何与领导同事交往到结婚对象,一切都由父亲来安排。在此之前,她父亲曾以断绝关系为由,要求她去指定单位面试,他始终不同意她现有的个人生活规划。
另外,考虑到家里同期的一个理财项目比较困难,毕业期间由于不稳定,她没有向父母要房租、旅游、生活、学习费用。“我爸妈问了我几次,我都说没有。他们以为我有实习有工作可能就真的有钱了,我也没还。”一旦“财务独立”的既定印象再次被打破,父母对人生规划的认知就会产生很大的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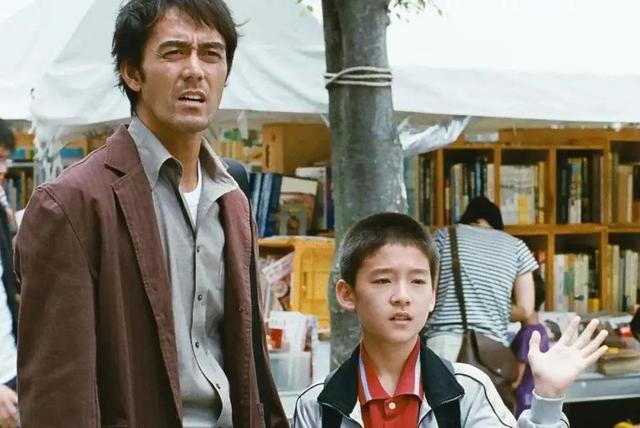
电影《比海更深》剧照
格林和张三的家庭情况不太一样,但她也从成长环境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消费观。格林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离婚了。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和父母关系疏远,父母给的生活费即使上了大学也是断断续续不稳定的。从大学开始,她没有生活费的时候就靠朋友资助。
渐渐地,这就发展成了某种人生哲学,“如果你想说你还不了我,但如果不得已,你还是可以给我的”。格林觉得向“机器”借钱比向朋友借钱容易,而且网贷平台太方便了,不用去银行办理各种手续。
因为上班时间早,艾比最早接触的信用卡就是贷款渠道。她算了一下贷款和花呗的利率,发现比她用的信用卡要高很多,于是决定不轻易使用。她勉强能负担借款的困难阶段,还没有考虑过让家里承担。但家里人知道,她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攒下钱,一直在还信用卡。“她一直觉得我有问题”。
艾比与父母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上,但他们之间的矛盾最终会落到金钱上。一直在国企工作的母亲经常指责艾比在其他熟人面前“抬不起头”,因为她不走一条套路。两个人的争吵往往是从为什么不结婚生孩子开始的。他们从不攒钱,但艾比不知道该如何报答父母为她付出的这么多。
在艾比的印象中,这套说辞从青春期开始就没怎么变过,但青春期的时候,她妈妈指责她学习不好,很没面子。艾比认为母亲想用这种说法来控制和干涉自己的生活。吵架吵到如此愤怒的时候,艾比甚至想,如果能把抚养她的钱全部还清,就可以断绝这段感情了。
艾比认为自己和上一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上一代人只为她的生活买单,没有自己。她经常跟妈妈说,要有自己的生活,希望她退休后能找一个像旅游或者跳舞这样的新爱好来填满生活,而不是总想着女儿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来打脸。但每次说到这个,她妈妈都会问艾比:“你要不要放过我?”
IV
自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80后和90后一直作为独生子女生活在歌唱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他们的童年,这一代人会被称为“小皇帝”或“小太阳”,以象征过度的关注和宠爱。
美国人类学家文丰曾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唯一希望——成年人》中解释过独生子女的亲子关系,这与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不得不相互竞争以赢得父母偏爱的情况不同。独生子女从出生开始就不必面对家庭资源的竞争,而且“作为所有父母的爱、投资和希望的唯一焦点,独生子女拥有巨大的权力。有时候,父母甚至要争夺独生子女的爱。"
独生子女一代长大后,会回头看那段时间的最爱,那凝聚着“唯一”的关心、爱和投入,享受着如此庞大的家庭资源,他们往往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关系控制和回报预期,但现实并不总是积极的,而是越来越残酷。
如今,搜索“被网贷毁掉的年轻人”这个标题,可以出现几十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描述网贷危害性的文章。这些文章抨击年轻人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过度虚荣,仿佛年轻人最大的伤害源就是年轻人自己。
根据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即在以富足和消费为特征的当代社会,“物”的意义不再局限于过去,主要特征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更多地具有符号的一般特征。人们在消费商品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费符号的意义,同时也在定义自己,认同群体。
比起谴责年轻人,更有意思的是,这一代年轻人不惜冒着被“毁灭”的风险,也要靠借贷来消费象征意义。这是什么?消费主义和虚荣所指向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那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就被承诺的。成长在高增长的时代,我们被许诺了所有的繁华和美好。我们被告知,只要我们努力爬上象征向上的梯子,我们最终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那里我们总是尽可能容易地获得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最好的东西。
努力工作的回报似乎太确切了,甚至有必要为整个家庭做出牺牲。几年后,画面变了,压力从社会蔓延到行业、家庭、个人,形成了某种亲子关系的底层张力,为每个年轻人提前消费借贷的故事埋下了种子。

电影剧照《夜空总是蓝色密度最高》
今年双十一到来之前,张三已经还清了所有网贷。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临时向朋友借的,但她不再需要承担不断增加的利息,也不会有新的贷款,甚至她彻底关闭了花呗。她原本打算在双十一期间购买近2000件护肤品,但仔细算了一下,发现真正的优惠力度并不大,于是放弃了。
现在她有一个理财计划,定期存钱。她的目标是先存够10万元。今年,我的一个朋友裸辞一点也不焦虑。她以为主要原因是朋友有10万存款。10万不算多,也做不了什么,但这是安全感的体现。好像10万后就可以告别不喜欢的工作和生活了。
艾比说,在疫情期间,她是“每片乌云都有一线希望”。疫情期间,她不能像以前一样出国旅游,之前的很多日常开销也省了。也是在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她终于还清了所有的信用卡。她只准备囤积一些猫粮,做一个低价的医美项目,主要是为了取悦自己。这一切的前提是她存了钱,而且这些消费后的储蓄卡里还有余额。
她还没有太多考虑未来的具体财务状况,也不考虑买房或者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也意味着安定下来。但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她甚至不确定以后会不会继续在北京工作。艾比笑着说:“如果我将来嫁给一个外国人怎么办?”真的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等八字缺了一个数字再做打算也不迟。"
格林的债务情况暂时没有好转,除了想办法每月还款,她暂时没有其他打算。在11月初的采访中,她不确定双十一要买什么。她可能会买一顶帽子。她现在还没有任何理财计划,但她也说过其实很想买房。“谁不想有房子,但是你知道我喜欢哪里的房子吗?”格林指着北京CBD的方向,说出了她之前去过的一个资深楼盘的名字。那里的二手房现在均价12.1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