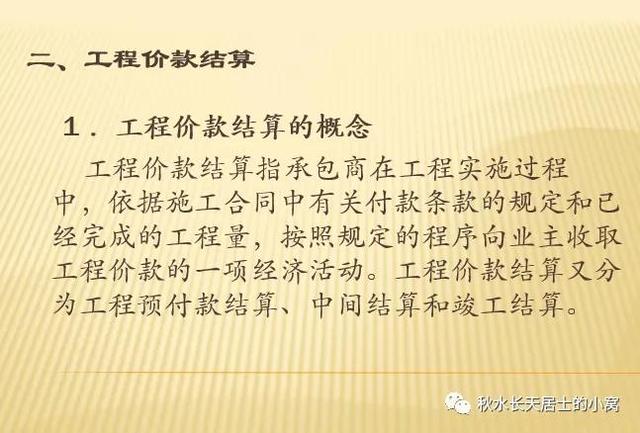
当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经竣工验收形成的《竣工验收报告》就建设房屋建筑面积作出不一致的确认时,房屋建筑面积结算依据的标准为何,这往往会在现实中形成纠纷,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其实在于结算依据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结算文件的问题。何为结算文件?一般认为结算文件是形成于发承包双方之间用于确定工程量最终结算造价的文件资料。那么,《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竣工验收报告》是否属于结算文件呢?似乎仍有争议。
众所周知,《竣工验收报告》是发包人在工程验收合格后向承包人出具的证明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报告,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建设单位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对工程勘察、涉及、施工、监理等方面的评价,工程竣工验收时间、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非结算行为的前提条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结算与竣工验收报告都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行为,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竣工验收报告所确定的房屋建筑面积作为结算依据是妥当的。
接下来,笔者再借助(2021)渝01民终932号民事判决书对这个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该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涉案房屋建筑面积的计算依据。该判决书分别从立法目的、形成时间、行为性质等方面评判房屋建筑面积结算依据,值得我们借鉴。这可谓比较全面的反映了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法律解释的问题。
首先,从立法目的看。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可见,建设工程的规划核实,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最重要的环节。建设工程从开工到竣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于建设单位的建设活动是否严格遵守规划许可要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需要进行监督检查。
具体而言,规划核实是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之前,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就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许可进行的检验,在对建设工程是否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件、附图确定的内容组织建设进行现场审核后,对于符合规划许可内容要求的,核发规划核实证明;对于经核实建设工程违反规划许可的,则及时依法提出处理意见;经规划核实不合格的或者未经规划核实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据此,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确认的规划核实建筑面积,从核实的方式、内容、目的看,均不宜直接作为建设工程发包人和承包人相关工程竣工结算面积的认定依据。
其次,从形成时间看。该案中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形成于2019年3月,《竣工验收报告》则形成于2019年4月,确认书形成在前、验收报告形成在后,该形成时间亦符合前述规定的要求,即经规划核实符合规划许可内容要求的,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核实证明后,建设单位可以依法组织竣工验收。同时也能证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针对房屋建筑面积作出的确认行为,并不能代替业主单位、施工单位及其他单位共同进行竣工验收这一施工过程中的必经环节,即在规划核实建筑面积之后,仍需发包人和承包人会同相关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共同确认案涉工程竣工的建筑面积。
最后,从行为性质看。进行竣工规划核实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法行使具体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为;而组织竣工验收则是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共同对施工内容进行检验的行为,验收后签字盖章确认的报告书,理应对发包人和承包人等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根据《竣工验收报告》载明的内容,发包人和承包人分别对涉案工程相应施工内容的建筑面积进行了确认,亦更符合双方对实际施工完成的建筑面积作出的真实表意。

建筑工程具有综合性,受到不同性质与层次的法律规范的规制,不同的规范,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后果,在这样的体系内,必须寻找规范与事实的链接点,看清楚背后的逻辑。例如,本案中体现出来的竣工规划核实与竣工验收所出具的法律文书在不一致的情况下,前者是行政监督管理行为,后者是承发包双方以及参与者之间的行为,何者可以作为结算的依据,首先需要厘清的是结算行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内涵,据此判断两份法律文件嫩否作为结算依据,这样考量问题才可能是符合逻辑的。
当然,该案的判决书法律适用中的法律解释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鞭辟入里,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焦点问题,进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虽然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有不同的争论,但就从案件事实以及法律规范的两大前提的认定与阐释中,法律逻辑一以贯之,这也是我们思考问题不可缺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