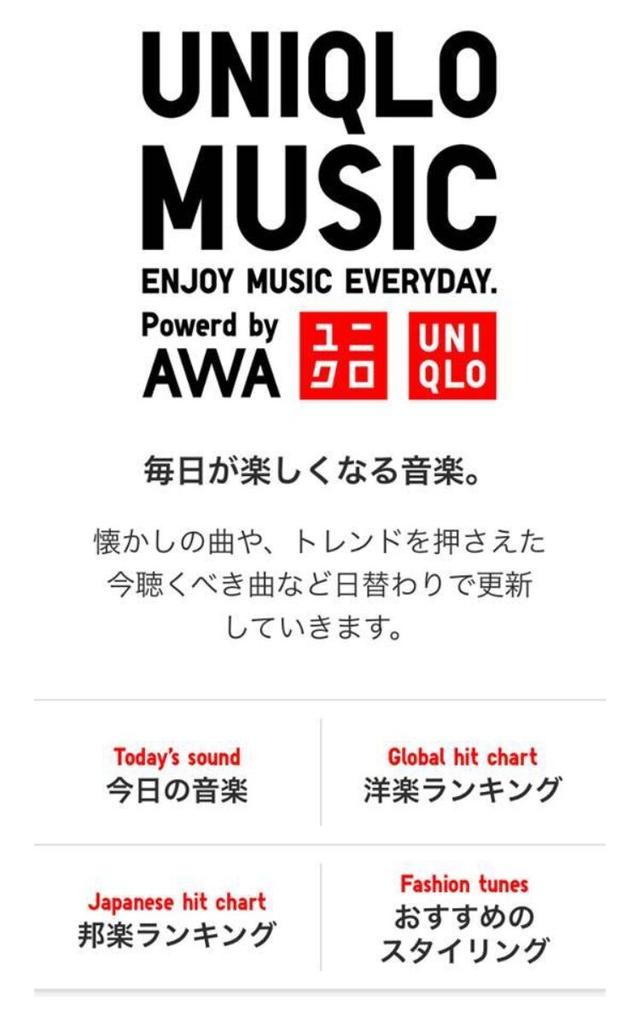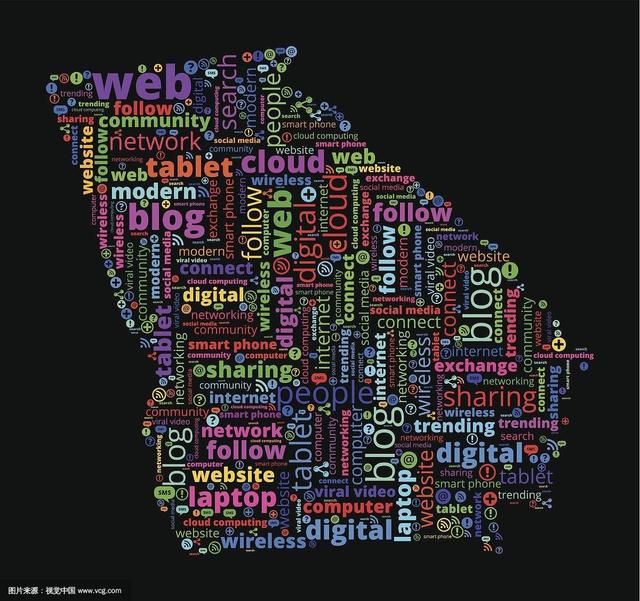
姜帅/文
TMT圈的人,现在介绍自己时都爱用“科技”这个词:科技行业,科技公司,科技媒体,科技记者,科技文章,科技产品等等。
什么是“科技”?有个很简单的答案:“科技”就是“科学&技术”,翻成英文就是science&technology,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非也。翻译是没问题的,但是在英文词典里,能找到“科学”的对应词science,也能找到“技术”的对应词technology,但怎么也找不到“科技”的对应词。
“科技”在中文里是一个词,但是要用英文翻译它,却非得用两个词,外加一个连接符。
词汇的差异背后,是事物的差异:“科技”在汉语世界里是个浑然的东西,但是在英语世界里,却是两个事物的结合,中间有一条怎么也擦不去的缝。
所以要了解“科技”这个词,最好先看看“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它的上位词。
科学中国人开始翻译science这个词是在清末。大翻译家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将science译成一个很美的词:“格致”,出处是儒家经典《大学》里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八条目”的头两条是圣贤学问的起步阶段,合称“格致”,字面意思是观察事物(格物),研究规律(致知)。比如理学大家王阳明,他在发明自己的“致良知”大义之前,曾有一段外求诸物的探索期。他曾经一本正经地在院子里“格竹”,盯着竹子看了好几天,累得大病一场。
可以说王阳明还是不太懂科学,他不懂要研究竹子,光看是不行的,还要动手,把竹子摘下来,切片,用玻璃夹起来,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甚至加以化验等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实验”,实验对科学是很重要的,可惜王阳明只会观察。
不过,观察虽然远远不够,但已属于科学行为,比如王阳明其实也可以走出院子,遍览大江南北不同的竹子品种,并且找出它们之间的形态异同,这叫植物形态学,也算是科学的一种。如果他再了不起一点,还可以像达尔文那样,探寻竹子物种的演化,甚至探讨竹子是从什么物种演化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严复用“格致”来翻译Science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后来严复翻译另一本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不知为何将science改译为“科学”。从那以后,“格致”与“科学”两种译法就并存着。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共和政权,将教育科目里的“格致”一科的名字改为“理科”,“格致”这个带有“封建味儿”的词用得就慢慢少了。
严复当然也不是使用“科学”一词的第一个中国人。有学者考证,康有为在1898年6月进呈光绪帝的“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一文中,有三处使用了“科学”,是这个词第一次在现代中国出现。
“科学”其实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借鉴来的。很多西方词汇的汉语译法,都是从日语中借来,比如“哲学”也是。有趣的是,“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译名(分别用来翻译science和philosophy)为同一位日本学者创造,他的名字叫西周。西周创造了很多这样的学术译名。
再向上追溯的话,西周之前,“科学”这个词就在日本出现了。大概从明治时期开始,日语中的“科学”一词被用来指代“分科之学”、“个别学问”。这也是西周“科学”这个译法的用意。“分门别类”的确是科学的重要特征,但绝不是唯一特征。和生动雅致的“格致”相比,“科学”这个译法就有很多东西被损失掉了。
永远不可能有完美的翻译。看一下science这个英文词本身吧,英文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又来自古希腊文episteme,意思是“知识”,并且是经过证明的、有普遍性的知识。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过知识本身也有高下之分,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三类:理论的、实践的、生产的。其中最好的知识是第一种:理论知识。理论知识又分三种:形而上学、数学、自然科学。
(当然,古希腊的自然科学,受哲学影响明显,主要是用哲学理论去解释朴素的日常观察,还不怎么懂得实验,特别是干预性、受控性的实验。)
为何理论知识是最好的?因为理论知识最关注原因,关注“为什么”。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其实是哲学的一部分。科学当时并没有独立性,科学只是哲学活动的一种。当时没有科学家,只有哲人。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几乎贯穿整个中世纪,13世纪时,经院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强调了实验的重要性,开始改变人们对scientia的理解,但他也仍然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下使用这个词。
约400年后,和他同名的一位哲学家,也是我们更熟悉的一位: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就是小品文写得很好的那一位),将实验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两位培根的思想非常相似),不仅在理论上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而且身体力行,亲自进行了大量科学实验。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的两大支柱: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培根竖起了一根:实验。据说他本人就是在解剖一只冰冻的鸡做实验时,受感染去世的。
可惜培根对数学的重视不够,后来这个缺憾由法国人弥补了。在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影响下,法国人特别重视数学,出了很多天才数学家,与海峡对岸重视实验的英国人相映成趣。
而将数学和实验两个方面完美地统一起来的人是牛顿,牛顿吸取了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等人的思想,以一系列伟大工作奠定了science这个词的现代含义:一种演绎(数学)与归纳(实验)相结合的系统思想方法。
靠着牛顿的威名,科学渐渐从哲学中彻底独立出来了,英文science一词也从此被用来指代数理化的实验科学。汉语的“科学”一词,基本与之对应。
值得一提的是德文对“科学”一词的处理。德文用Wissenschaft这个词来翻译拉丁文scientia,但是和英文译法science不同,Wissenschaft不光指代自然科学,也包括了数学和社会科学,乃至包罗一切系统的、有严格方法的知识。
这显然比science要宽了不少,所以有的汉语学者不将德文Wissenschaft一词译为“科学”,而译为“知识学”。这又有点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味道。
无论如何,“科学”这个词有一个维度,始终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那就是一种纯理论、非实用的旨趣。科学可以被用来造福人类,但是科学本身不以人类福利为目的。毋宁说科学是一场游戏,高级的智力游戏。
技术第一个使用汉语“技术”这个词的,不是技术大牛,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这里的“技术”其实与现代的意义很接近,意为“技艺”、“方术”。
当然,“技术”作为一个现代汉语词汇,也是个殖民化词汇,它对应的是英文technology。第一个采用这个译法的是谁,有待考证。
至于英文technology的历史,也比science要短暂的多,直到17世纪才在英语里出现,指各种技艺。1859年technology正式进入英语词典。到20世纪后半叶,technology被定义为“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
像很多“高大上”的英文单词一样,technology也是源自古希腊语,它是两个词的组合:techne(技艺、技能、工艺)和logos(言辞、道),合起来的意思大概就是“技艺之道”。其中techne的意思是指所有与自然相区别的人类活动,特别是一种技能性的、非自然本能的活动。比如呼吸、便溺不能算作是techne,直立行走勉强算是techne,使用火、计算、开车等等,才算正宗的techne。
不难发现technology和science的明显差别:technology有一种强烈的实用性、实践性,目的往往是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和智力游戏。
科技“科技”作为一个英语中找不到的词(不敢说只能在汉语中找到),只能用science&technology来对译,也就是“科学&技术”。很显然,这是一个缩略词,因为“科学技术”四个字太长了,所以就减缩成“科技”两个字。
这是汉语中常见的做法,比如“对外贸易”减缩成“外贸”,“公共交通”减缩成“公交”,“风险投资”减缩成“风投”等等。
但是“科技”这个词有些特殊,它的两个上位词之间——“科学”和“技术”——有着容易被忽视的微妙区别。两者含义迥然不同,却又容易一笔带过,“科技”这个缩略用法,其实是大大助长了这种马虎的。

汉语世界中谁第一次使用“科技”这个词,截至发稿已来不及考证,只能等待有心人了。但是“科技”给人的印象,总是有些强调技术而忽视科学,强调实用而忽视理论。中国在被驱赶进现代文明之前,对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比较陌生,对那种不计功利,不求变现,只图个好玩的探索精神不太宽容,这或许是诞生“科技”这个缩略用法的土壤。
日常语言是很精明的,它不会为了自以为不重要的事物,多费哪怕一个音节。
TMT圈里的“科技”言归正传。为何TMT圈里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科技”这个词自指?看看各大门户网站的“科技频道”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是互联网行业、通信行业乃至新媒体行业的资讯。而且,这些资讯有时并无半点科学或者技术的内容,有时是产业资讯,有时是政策资讯,有时甚至是人物传记、产品广告等等。
首先,在TMT领域,“科技”这个词的语义发生了缩减。只要让这行里的人反思,他们就能立刻察觉这一点。所谓“科技”有太多领域了,比如古生物研究,比如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理论,比如深海探测,比如地震研究,比如手术和药物上的种种临床进展等等。
(问题是,为何有的科技内容,比如机器人,比如自动驾驶,比如量子通信,能挤进门户网站的科技频道,其他的却挤不进去呢?)
其次,“科技”这个词的语义在缩减的同时,也发生了扩张。比如一个电商公司和另一个电商公司的促销口水战,一个网约车平台拿到了运营资质牌照,一个外卖平台又进行了新的融资等等,这些本不是科技领域的话题,也被当做“科技”来报导。
“科技”这个词在TMT领域里的变形是个事实,它的基础是TMT从业者的无意识。相对于用“反思”轻易地取消它的存在,研究这种无意识的起因显然更有价值。但这个研究很困难,在此只能尝试给出一点猜测。
不可否认的是,TMT领域本身有科技基础,它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一条资讯越与信息科技沾边,就越容易被放行进入“科技频道”,其他的就对不起了。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信息科技早已走出了实验室,开始了大规模、多层次的商用,衍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产业形态,其中很大一部分还直接触达了普通消费者,重新形塑了他们的生活乃至意识。比如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再比如以手机定位和匹配算法为基础的Uber和滴滴。
科技在专家的头脑里也好,在实验室里也好,都不会产生显著的传播效应,而注定是极少数人的资源。科技只有落地,成为商业,走进万千普通人的生活,融入复杂浩瀚的场景,才有传播效应,像进入了万花筒。
在这一点上,信息科技是最时髦的科技,比其他科技都时髦。
但概念都是有时延的。名字的改变,永远比事物本身改变得慢。当很多信息科技已经在大规模商用当中固化、模式化,从而让不懂个中机理的人也能运营或消费时,人们却还在用旧的名字来称呼它。
此外还有一个更好理解的原因:信息科技从开发到商业变现的周期,以及自身迭代更新的周期,比以往任何技术都要短,都要快,都要频繁。这也使得TMT行业永远无法抽离技术维度。随随便便一个革命性的技术迭代,就可以颠覆一批传统的公司,造就一批新公司。这一行必须始终紧跟最新的技术动向,对之保持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