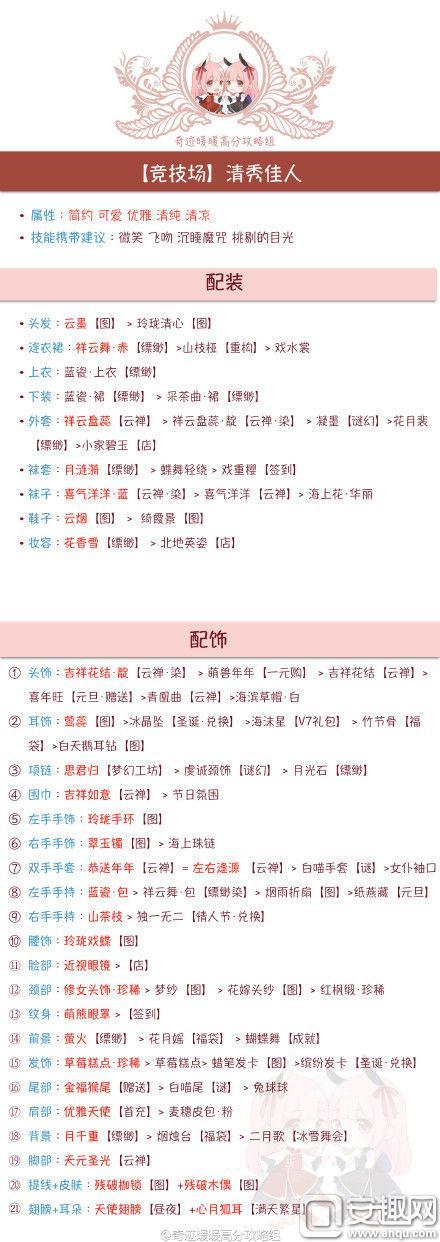五二
以“豪放”为“神味”一义之内质精神,非余偶然兴会之所至,盖有由来者亦其远矣,一以贯之者亦其久矣。豪放之精神,余尝阐论之于《金庸说部诗学论稿》一作《〈笑傲江湖〉之精神》一章,其言曰:
豪放者,历经最大束缚而获得之自由之境也,戴枷锁而能舞也,于事物之本质得玲珑剔透之领悟,而与其生命存在之节奏相俯仰感应,得物我之间莫大之和谐,而又使我之性情适乎天地万物,缘世俗民生而臻致“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出入人天,而又呈现为烂熳之状态者也。其核心内涵则不受拘束,故豪放乃事物演进之内因,亦我性与于创造之表现也。纯粹之豪放,其生命力恒及于宇宙自然而以物待我,故能于虚应万物,以我性改造自然人生者也。豪放之我性,必不徇于物,而保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其所徇于物者,物之自然也,无之,物不得其生焉;必不徇我也,其所徇,乃芸芸众生之大者,故由之得以成就灿烂烂熳之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也。豪放之境界,写意之所生也,以动为其本色也,以历虚而虚实互生之境为其结构,其心境不可下于冲和平淡也。故豪放一义,非仅疏旷放达即所谓达观而已,而必兼达观与积极两种精神境界;故如词中苏东坡之豪放,未辛稼轩若也。
世俗之所云豪放,多肤浅之论,往往在风格论之层次,虽与豪放之精神相关,而与其最佳无上之义谛,相去远矣。豪放一义乃东方文化精神之最高境界,虽儒道二家之极致,不足以当之也。必和合儒、道二家之积极、进步之精神而补其未善,而后可以当之也。豪放之境为吾国特有,唯有此特质,乃能使艺术在形式上直抒性情,不拘格套,姿态烂熳,在内容上富有活力,情趣不俗,气质大方,表现为积极乐观之精神境界。西方之勇武强壮、威猛庄严,与豪放无涉,西方人不含此特质,亦不解豪放为何物。西方人之情感以激情为形态,其潇洒在形体,东方豪放之本质则在于精神。即以释氏言之,其清净庄严、玄秘精深之境界,亦不蕴含豪放之精神。豪放存在之环境,亦由吾国两千年酝酿而成之人格化之事物为其氛围,事物或缘古之意境理论而不尽适于今,若洒脱不羁、姿态烂熳之我性,则无古无今,越度时空,如魏晋南北朝时达观放荡之士之性情,明季激进自由之士(如李贽)之性情,无不灿烂于千古,永恒于历史。又豪放之得,必历“悟”之境,然如释氏,如中土之禅宗,专以之为事,如六祖慧能与历代高僧之故事,其行亦或放荡不羁,自由不拘,睥睨俗世,脱弃红尘,空色自如,不执于物,然以吾人之目光视之,此可谓之达观,不可谓之乐观,不可谓之积极,故非豪放。其于世也,虽期诸普度,实限以自证,世俗中人之智计,又不可期之以遍悟也。历代高僧犹有数十年不悟者,况世俗中人哉。盖释氏空悟义理,自陷抽象,其所行止、尊崇,不过如瓶中之花、镜中之象、空中之音、水中之月,去真实存在之境界,隔一层矣,故云自我圆满,实不关人痛痒,普度众生,便如雾中观花光景。盖自然人生之真谛,不患现实世俗,而患罔能超越世俗。红尘世俗,大美存焉。释氏之所为,实无异缘木求鱼,脱离世俗。超越如蜂采花而酿为蜜;脱离乃避开世俗,自求虚拟理想之境,如“蝶飞蛹外茧成全”之句所揭,不过蛹化为蝶。蜜不可复成为花,故其过程,乃一创造之提升;蝶可复产卵而成蛹,故其过程,乃一机械之循环。此两种境界,一名大我,一名小我。大我乃于平凡、寻常中造就非凡,小我则因人禀赋因缘之异以成,不可强求。故豪放之境,必是大我,即“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能于此者,乃真豪放也。
豪放之为精神境界、精神意态,为自信,为烂熳也。东坡《卜算子》之“拣尽寒枝不肯栖,缥缈孤鸿影”,不具自信也。若《定风波》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则可矣。又如张于湖《念奴娇》之“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严蕊《卜算子》之“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李太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之“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必具自信而不待于外物,乃堪与于豪放也。豪放之事物之本质,在其生命力内蕴之美之闳大充实,无物可以挫之败之而能阻挡其向完美完善之境发展之趋势,亦即事物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者,亦即《〈聊斋志异•婴宁〉之意境神味》所言“外形实不足以掩其内美”黄蓉之例之义旨。又如屈大均《鲁连台》诗云:“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无限自信之意态,又何如也。《庄子》有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则大美存焉”,是何等自信之境界;若“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必言矣。必具自信之美,而后能摒绝浮躁繁华,离于色相,而能与物交融心会,固守孤独寂寞,寄其形骸,探其真美。发之于外,乃见动媚烂漫。按“媚”之一语,实即内蕴之美之主于静而动而烂熳者,内媚而外烂熳,皆为英姿勃发深具自信之豪放者所有,皆摄人心魄、澡雪精神之美也,必具自信,乃能如是也。西人莱辛之《拉奥孔》有“化美为媚”之一法,虽倡动态之美,而于内美(人格、思想、精神境界之美)仍在门外,亦不可期以豪放之精神也。
吾国文学中诗人之最具豪放之气质者,其杜少陵、李太白、关汉卿、辛稼轩数子者欤?其次则苏东坡、龚定庵辈。文学虽未大见而人极豪放者,则嵇康也。以书为论,则颠张狂素之大草也。或能解李太白之豪放,而不能解杜少陵之豪放,而欧阳修《六一诗话》有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务以精意相高”,则其豪放为确然无疑也。词人不得不独许苏、辛者,盖二人之后之所谓豪放派,实鲜蕴含豪放之精神也。关汉卿之豪放,乃元曲以豪放为本色之最出色者。龚定庵之豪放,则异于李太白之清华莹澈、玉雪皎洁,而透露瑰丽奇谲、一往情深之色彩,未易多得也。或以如放翁“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之句者为豪放,实则豪放并非依于雄大壮阔之境,亦不喜以热烈奔放为主,而大致在动中孕静,静乃我性和谐于物之表现,动则寓我之内美于其中,故如稼轩词中之写乡村闲适者,虽貌似静,而其内在所蕴含勃郁超逸、深浑优美之人格、情志、理想则丝毫未减未逊,无往而非具豪放之精神者也。
豪放之精神必饱含深情,于自然人生之事、理、意、趣,所谓千形万态之色相,能欣赏其美,而以陶冶怡养性情,葆持虚盈之态,貌似极静,极无所事事,实则物极而反,待时以动,身心精神,皆极灵动,如蛇信然。豪放之精神在于胜己,而非溺陷于世俗,争扰于名利。由胜自然以提升自我,而非以人为的,以辱、败、陷、杀之为满足,亦不以玩性情为代价,亦不重世俗之名利,所谓天下交誉之而不加其喜,天下交毁之而不加其忧焉而已。故真正具豪放之精神者,不以名利富贵为意志,而能以布衣傲王侯。亦非傲之,不过视之如稚子赤裸之时,人人不异也。故真正具豪放之精神者,必爱人,必以仁待人,以平等待人,以平常心处世,而尤对世俗中人之弱者饱含深情,而能以其生为一己之喜恕哀乐,而恒欲其生得大美满幸福。然现实世界之民生又恒不得善,恒为名利所曲,权贵所迫,为恶劣秽丑所污辱毁灭,故豪放者常能舍一己之私而起与之争,而能不以生死为意,林少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之句,得其实矣,纵身死之,犹得“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也。吾人之览杜诗,深郁固佳,而其中随处而有之深情,尤使人不能自持。故真正具豪放之精神者,其性情必特出,其大而可观者则成烂熳,而能入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亦唯此种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而能有灿烂伟大之成就也。纵生不逢时,亦由之足以欣赏自然人生,悠然笑傲江湖、林下、市街以终,不可以哉!如子路之将死正冠,虽有其迂而腐;而嵇康之临刑弹琴一曲,何其洒脱风流也!王右丞有句云:“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宇宙自然人生之气象,如是而已,必得此生生不息、大气深情之天地气韵之领悟,而后乃能于豪放之精神有深解也。嗟夫,后世之人,孰可与言乎豪放者哉!……
豪放之精神,意中之豪放也,故如令狐冲之被迫而起,而成淡然悠远、浑涵一切之气象,即其正色也。若能以实现,则其出色也。如萧峰之豪放,多具现实世界之色彩,而以阳刚大气之美为主,慷慨激昂而一往情深,于惨痛激烈之中,以成生命精神之异彩,方之令狐冲,一刚烈正气,一虚静灵秀,豪放之禀斯二美,亦足以移人矣。若崇豪放而不解其精神,诚乡愿者矣。如嵇康诗之“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微啸清风,鼓檝容裔”者,豪放之意态何其挥洒自然也。唯有此种豪放之意态,乃能为《与山巨源绝交书》也,孟子所言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而内又“善养吾浩然之气”,则洵豪放者之能事矣。令狐冲与萧峰,皆足以当之也。若夫享富贵之清华而不务实事世务,为而又仅止于其身,或孤芳自赏,或三五麋聚,终日耽于诗酒,溺于声伎,自称傲啸山林朝市,其实外强中干,事起则变节,自降身为妇人女子,似此之人,虽有豪放之行,之意态,而玷污豪放之精神矣。盖豪放之精神之所本,为真淳朴素之性情所具之内美,由兹内美,生诸意态,则无往而非豪放,故吾人观《神雕侠侣》中之杨过,而觉其豪放之气质,远不如郭靖为多,即此理也。又如周伯通,性情虽佳,终不可以豪放目之者,以去现实世界之利害关系已远之故也;又如左冷禅、岳不群诸人,即之过近而不能超脱物外,亦不足为豪放之境界也。
其论既以《笑傲江湖》为主,则武侠小说中之江湖本有超世虚幻之色彩,故所论豪放之精神,总体仍在词中苏轼之豪放境界,如令狐冲虽能豪放而淡泊名利,然终于世俗民生无所与,而唯归隐一途也。若萧峰之欲用世,而不得其用,欲于归隐有所突破而不能得,则亦惟自尽一途,以升入崇高之境界,此亦足见武侠小说不足与于豪放之最高境界,若词中辛稼轩之精神境界,则又不可不知者也。
又拙撰《论豪放》,古今由范畴而论豪放之最全面,评价最高者也。由复兴吾国以壮美为主之审美理想为其心,凡义界内涵、特点、结构生成及生成之流程、与相关相似范畴之辨正、历史上之发展嬗变、思想精神及哲学辩证法及诗学之基础、文艺中之表现及审美意蕴、诗学词学之理论探讨诸问题,皆一一明辨详论之。今暂择其要略之义如次:豪放之为一范畴也,为吾国文论范畴中最具主体性精神色彩者,故最具创新之精神,最富创造力。其义一以贯之于美学范畴、诗学范畴、词学范畴、曲学范畴,其中美学可涵书法绘画,而诗学可涵词曲之学,要之,词学是其理论纠缠之核心,而诗学是其主体之所在。豪放之逻辑起点为以“气”为主之“收”与“放”之动态关系,孙联奎《诗品臆说》云:“惟有豪放之气,乃有豪放之诗”,是矣。其广义为风格论,与阴柔美相对待,狭义与婉约相对待。豪放之内涵,核心之点为气魄大而不守拘束,进而言其精,则主体因其志意理想接于世俗民生而得之气(至于盛大充沛之境)与情(热烈深情)而成就一“无我之上之有我”,而能不守既有过时、僵化之礼法制度、规律法则之束缚也。故豪放为主体不隔于世俗民生之必然结果,凡能成就“无我之上之有我”者,必能见为豪放之境界。具体而言其适用领域则分三层次:社会人生、技艺表达及风格形态,分别对应礼法制度、规律及婉约(实可扩大为“优美”)。自表达形态而言,则与豪放对立者为“恭谨”、“墨守成规”、“含蓄”。“豪放”内在结构亦阴阳刚柔和合之最佳者,他如“豪宕”、“豪迈”、“豪雅”、“豪雄”、“豪壮”、“豪纵”、“豪诞”、“豪恣”、“放逸”、“放达”、“放旷”、“放肆”、“放浪”(其外围尚有“狂放”、“旷达”、“雄浑”、“狂狷”之类,皆可视为两者之中间状态),皆有所不足。如“豪宕”总体以阳刚为主,而其中之“宕”则阳刚有过;“豪雅”总体以阴柔为主,其中之“雅”则又阴柔稍过。唯“豪放”之“豪”在内,其为气之积聚也,以阴柔而聚此阳刚之物,未发之前,属总体阴柔之状态,而“放”为气之发,因其盛大充沛而总体阳刚,其发之也控制自如,婉转变化,则又涵阴柔之处,两者和合为“豪放”,为内外合一、阴阳和谐之最佳动态结构,为诸范畴所无也。“婉约”之“婉”、“约”皆偏于阴柔,总体而乏阳刚,乃其不可弥补之缺陷,岂能与“豪放”比方哉!鲜明强烈之主体性精神特征,盛大充沛之内在气蕴、外在气势,直抒胸臆、淋漓尽致之表达方式,此豪放之三大特点也。吾国历史上之“中和”有二,一则以《易传》积极进取、阳刚刚健精神为主,一则以老庄消极逍遥、柔弱超逸为主,豪放则合两者之长,为积极之“中和”之境界。“豪放”为诸“壮美”风格中最具主体性精神色彩者,为“壮美”之高级形态,未必见为“壮美”之一般特征,若无主体精神之豪放,虽壮阔壮丽而非豪放也。“壮美”偏于写实、再现而“豪放”偏于写意、表现(因更多主体精神之介入)。西人之“崇高”为主于心之境界,豪放则以现实为心,当今崇高已为荒诞所替,崇高感已大失,故未如豪放更具现实性也。“浪漫主义”之核心思想在个性解放,此或有益于豪放,而豪放之高境则不独见为浪漫之境界,明人文艺浪漫主义色彩大兴,而又大具世俗之意蕴,而不见为豪放,即其证据也。西人尼采《悲剧之诞生》论浪漫主义之失,良足参证也。豪放萌芽于先秦,生发于汉,如《史记》之人物传记是其代表。及于魏晋,玄学为定于一尊而后已趋庸俗之儒学之反动,豪放复振,然姿态尚未大足,唯鲍照起于民间,悲壮豪放,灿烂一代。至于唐之恢宏开放,遂大兴于歌诗、书法,李、杜为盛唐歌诗之代表,皆以豪放为胜境也。有宋诗衰而词胜,风格卑弱,豪放为壮美风格之代表先锋而与婉约对待,已见俗文学兴起之端倪,周、姜、吴、张之流不知以世俗补其气、情,词遂雅化而衰。至元曲之再变,世俗之姿态大见,豪放遂为其确然无疑之本色正宗。元曲得成“一代之文学”者,功多在剧曲,今人多承唐诗、宋词、元曲之皆为歌诗而为“一代之文学”,而以元散曲为诗词之正脉而排斥剧曲之非歌诗,不知若仅散曲,初非能当得“一代之文学”之誉也,“一代之文学”如汉赋、晋文及明清小说,并非以歌诗为线索也。剧曲为吾国歌诗之极致,为叙事诗之大成,为抒情诗之开拓,为意境理论之开拓,为俗文学之开拓,今人未必知之也。令雅套俗,剧曲实即套之串连,若以令多雅而以清丽为事为其本色,则大误矣,故余以为任中敏《散曲概论》以豪放为散曲之本色,虽本即其实,而实具旷古未有之功也,惜今人治曲者多昧之矣。有清词学,渐见豪放、婉约皆为本色之音,如田同之《西圃词说》、沈祥龙《论词随笔》。近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若郭沫若之新诗、康有为、吴昌硕、傅抱石之书画及新派武侠小说,皆大兴豪放之精神,壮心可嘉;当代则又微矣。豪放之义,为儒道互补和合取长补短之最佳结晶,承诗“可以怨”之精神而大反为政教思想庸俗之“温柔敦厚”,近人陈独秀、鲁迅皆斥以阴柔柔弱为主之审美理想之非。以“活”为辩证法之人生境界,天真、朴素、本色之人格本真架构,自信热烈、一往情深之心灵世界,诗酒豪放、琴剑炫异之人生意态,此豪放之四大审美意蕴也。豪放在诗学词学领域之诸问题,要在见之为豪放、婉约之辨,余括之为六义:“豪放”为“婉约”之突破与发展,为不隔于世俗民生及确立主体个性精神而至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之必然结果;“豪放”词可兼有“婉约”词之长,反之则不然;“豪放”、“婉约”皆词之本色;“豪放”非“诗化词”,诗、词、曲皆诗也,皆须达致诗之最高境界,自诗观之,则“豪放”为诗之最高境界而“婉约”非是;“豪放”、“婉约”二分法非粗略,他种细分之风格亦有,然唯于此两种风格之对待上,乃能领略其于“豪放”成熟为一范畴而至于其极限之点之意义,若自他种细分种种不一之风格观之,则不可得是也;“豪放”为唐诗宋词元曲一脉相承之内在精神,为其最高境界之所在,是诗、词、曲形式演变之内在动力之所自,此非“婉约”所能办也。豪放之价值为吾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根本精神,为以壮美为主之审美理想重建之根本精神,为继承发展传统文化、评价传统文艺之新线索新基准。若具此豪放之精神、眼光,则吾国之传统文化当自能出新境界也。传统词学批评豪放之缺点,非豪放之最高境界,而若论豪放、婉约二者之是非长短,则必自其最高境界以观之,又何疑也。故豪放之最高境界如辛稼轩之词、关汉卿之剧曲,岂受其责哉!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云:“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不知“意境”理论本即笼罩辛词不住也。若犹然以“意境”之眼光以观豪放,则其于豪放缺点之评价也宜然也,岂公论哉!
五三
“神味”、“意境”(以王国维之“境界”为最高形态)二义,余尝论其异而得数端者焉,而综“神味”一旨之要义若干,其次如下:
1.“神味”兼静态而以动态美为主,其最高之姿态为泼辣烂漫,以此为切入现实世界之契机(虚实互生,以实为主。虚所以提升提炼实而得其精华,以入于更高境界之实)。此一动静非形式上者,而由精神主之者也。形式上之动仅得活泼之韵致风神,精神上者则得灵媚闳美,皆我之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之所注者也。
2.“神味”重内美,而重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此与“意境”美大异。“意境”之哲学基础为“天人合一”,诗学基础为“中和”之美,但得其偏于消极静态柔弱者;“神味”则以此为非是终境,而最终以人主之而见人之主体性精神,而得“中和”之美之偏于积极刚健动态者,并兼有“意境”之长者也。惟是之故,豪放词乃能兼有婉约词之长,而反是则不然也。
3.人或人物形象及其存在之最高境界:“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此一境界由进王国维之“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而得。传神合消极之“我”(可能为“大我”)为意境,而传神合积极之“大我”(即“无我之上之有我”)为“神味”。欲至于“大我”之境界,必以非功利之态度对人而以人为第一位之价值而后可得也。
4.“神味”说之三要素:事、意、细节,而以性情一之;性情尤重朴素,由天真而至烂漫,得人间“大我”之情味而至泼辣、豪放。若无性情中之朴素天真,断不能至于豪放泼辣之境界也。
5.“神味”之内质:豪放之精神境界。“意境”以写意为极致,“神味”以豪放为极致。“意境”以“兴象”为中心、以情景为中心,“神味”以“细节”为中心、以人之主体性精神为中心。
6.“神味”之本质特征:不可复(性情、细节)。“意境”则多复而大同小异,此由“情”、“景”易单调故也,而唐以后之诗史足以证之。“神味”之“味”,特指“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经于世俗而后得者,故其性无二,而不可复也。
7.“神味”创造之理想:由大俗而臻大雅,其境界为平凡而造伟美,闳大深情,不可方物,不可思议。非独如审美,可以闲淡之姿态心神以观佳人,而是和合真、善、美三者,若睹佳人而当下呆立,魂灵出窍,得大受用也。
8.三境界之别:艺术以灵动为特色,人生以“意境”(尚淡远闲逸)为特色,文学以神味(“神”为物之极,“味”为人之极)为特色。文学亦艺术之一,而含未实现之人生,故最全面而深刻,深具理想之色彩也。
9.“神味”为杂多融一之美,以天真烂漫、淋漓尽致为外在最高之表现形态。“神”为一物之极致,“味”为多物或人与物和合之极致。“神”之最高义在于性情之神,“味”之最高义在于以人为最无价最第一之价值之境界而得之“味”。
10.比喻:“意境”如王士禛所言之龙,云中只露一鳞一爪;“神味”如张僧繇之画龙点睛。“意境”如鲲鹏乘风,“神味”如凤凰涅槃。“意境”如水中之盐味、蛹中之蝶,“神味”如蜜中之花、火中之凤。
11.“意境”典范代表之作如李易安之《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其稍巨者则如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神味”典范之作如《挂枝儿》(“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其闳大者则如关汉卿之《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感天动地窦娥冤》。
12.“神味”说之目的:理论上为突破“意境”,故文学上为促使开一新境界而别造兴盛,人生则为人而以人为最无价之价值、以人为第一位之价值也。以人为最第一之价值,非以人为中心,而抹杀其他一切诸价值者也。
13.创造之法之异:“意境”,由有限以求无限,故其所求之“大我”仍为个体之“小我”,为形式上之“大我”也;“神味”,则是将有限最佳化,故其所求之“大我”乃是“无我之上之有我”,由世俗之社会民生锻炼而来者也。
14.王静安之“不隔”,乃就情景以言,此特小事耳,已隔一层,此断不能至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身之融入现实世俗世界,而后有感情境界,而后有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亦即大俗之境界,豪放之境界,此真不隔也。“不隔”之义,用之未必能至于“大我”之境界即“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无之必不能至于“大我”之境界者也。
15.“意境”以陶渊明所造之境界为最高境界,而“神味”则以辛稼轩所造之境界为最高境界,而无论其文学之境界也,无论其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也。以文学境界论,李杜自居最第一,而其人格境界比之辛稼轩尚有所稍逊,况辛稼轩之文学境界足以高于陶渊明,故以辛稼轩对待陶渊明也。
16.“意境”之总体氛围为优美,特以抒情诗为其范围;“神味”之总体氛围则为偏于壮美而兼优美,抒情、叙事皆总有之而不分你我,而鉴于吾国抒情诗特已发达之甚之事实,故今后其寄托特在叙事诗一体。故“意境”一情景为内外,而“神味”则内则以“豪放”之精神,外则以“细节”见也。
17.由言不尽意至于求象外之象、味外之味、意外之旨,而加以吾国文化精神中中和之消极柔弱,此“意境”之实质,虽王静安之“境界”说,亦不过如此,此特为“技”之境界耳,是守成之境界也;若由之而更进,得中和之积极阳刚,由之以见人之主体精神即动之精神,以为融入现实世俗世界之契机,则创造之境界遂可期,是“神味”一旨之精神也。
18.“意境”者审美鉴赏之理论也,其非不能于创造美也,而审美鉴赏是其最适于用者也,审美鉴赏之境界是其所求所赏也;“神味”则审美鉴赏而兼创造美之理论也,而创造精神为其内核,以“豪放”之本质即为不受拘束于业已僵化而丧失生机之礼法制度、法则规范也。故“意境”用于古则可,用于今后而有以进益文学创作,则非是第一义矣。
19.“意境”之最终目的为由文学而及人生,“神味”之最终目的则由文学而及人。为人生,则不无现实功利之影响;为人,则是以人为第一位之价值也,为成就人也。近世西人大崇个性,故以群性为指归之“崇高”得大兴起,吾国自汉代后即大崇群性而乏个性,故豪放得造极于元人粗略之治。豪放者,由群性成就个性之具者也,故近世西人所大崇举之“崇高”之境界,唯由“豪放”而可得瓜葛,若准之吾国,则豪放是其出头地也。
统观诸义,可略得“神味”说之所以也,而若欲于上述“神味”一旨诸要义有真切而鲜明之体悟,则非合观拙作《嫁笛聘箫楼曲话》、《<人间词话>评说》、《诸二十四诗品》不办也。
五四
余之论诗也,起于创作。十七年前,余始作为者为新诗,然时新诗已陷入困境,困惑而不知前路何在,故又习旧体诗,兼观其诗学,欲承传统诗学之长,而加以改进,以为新诗觅一可行之路径也。今回顾新诗三十年来之所成就,可谓驳杂多端,由最初之辉煌而影响于社会,终归于文学之“边缘化”流程之中,而渐成诗人之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矣。其所开拓处,则仍欲以西学张之,至今已基本完成西人曾经眼花缭乱之所有花样翻新,佳诗之所有要素如情感、形式、姿态、自我等,皆所涵有,然无一人能集萃众美,由所变化之新境界以取得具审美理想境界之诗美,而为后来者立一典范也。新诗史惟有风云变幻,却甚乏经典,原之,则新诗三十年来已完成主体个性之造就,而其所有作为,亦不出个性一己小我之经营而外,虽与政治意识形态之直接关系脱离,然始终未能回归造就“大我”之境界之路径;唯其以个性为着眼点,故诗之知性过于诗性,诗人好以思想、知识、个体生命体验寄之以见广大深博,而又未能吸收融化西学入其血脉、精神之中,粗廓梗略者多,独立生发者寡,终是随人短长之境,以此为胜,离于诗意之境界亦且远矣!西人若见吾国诗人之拾其唾余,笑必灿烂矣!若非我者,拉杂终究不似。故新诗之最大误区,乃是表现思想,若欲表现思想之深邃独特,则不必诗也。总之,个性——无论其至于如何奇幻深邃之境界,却非诗之终极境界,非诗之最高境界也。今之新诗人犹以个性为其所有用心之所在,诚可惜也。诗人煞费苦心寻找诗并借得若干外援,而始终无法回到诗之真正中心,或未成为其本身即诗之境界,亦三十年来新诗之最大悲剧也。诗之开拓若不与现实境界相合,而流于个性变幻之“为艺术而艺术”之境界,若不变此路径,无论三十年,即百年其面目亦不得根本之改变也。故余为新诗指一路向云:“个性且休矣!思想且休矣!且向世俗民生抛血泪、讨活计去!”
五五
诗者,人之自我生命存在之最高形式、最高姿态、最高境界,以人为最第一之价值之境界,以臻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得其神味者也。臻于此一“神味”之“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纯是一片情与气之光影交织缠绵而淋漓,情为主体之喷薄,其寄托若不可胜,气为主体之接于世俗民生而得之磅礴浩然者,其所向也若不可遏。诗非独为一切诸艺之最高形式,且为世间人之所以为人者所能达致之最高境界、最高可能,为人提升自我之最佳途径也。小说容量亦且丰厚深邃,然以代言为胜,难于寄托主体浸透整个生命、经历整个世界之情感、意志,其所持之之姿态,颇有不如也。
世界之本质,必以人为始,以人为终;以人为世界基础、本原之最大成者,而世界之大成又终将归之于人者也。鲁迅《文化偏至论》云:“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我性之绝对自由而不守任何外物之束缚,古今中外之范畴,惟“豪放”最具此一精神之境界。黑格尔之“绝对精神”、王阳明之“良知”,或误其始,或误其终,皆非全完者。以是之故,余命诗而如此也。此一义也,乃诗之最高义,他者之义亦或有诗意,则皆其下者,余并不一概抹杀也。余以此义示昌邑宋伟杰,云:“人之最高境界即诗也。”嗟乎,慧哉,亦可谓其提纲挈领者矣!宋君,治外国文学者也。又吴冠中云:“诗才是最高的艺术境界”(“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鲁迅,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态,越到晚年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诗才是最高的艺术境界。”)道此言语时,吴氏已然九十高龄,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此则可谓将殁而悟,亦无不可也。所惜者,其所悟者亦常理耳,诗画一理本为吾国谈艺常言,故古之歌诗往往以意境为高,此乃画境之极致,实非诗之最高境界也。西人莱辛《拉奥孔》一书早析论诗之最高境界高于绘画(雕塑)之最高境界之理,近人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亦究论吾国画境之极致非诗之最高境界。吴氏之言犹以艺术为心,此正其最大之缺陷,故虽若悟而实未悟,遑论透彻之悟矣!其虽论乎技巧不如内涵,然以艺术境界目诗,仍属“技”之境界,犹非以人之本质之高度以明之者也。况悟本寻常事,若止于悟,犹非足道者也!吴先生穷毕生之力,欲于画境而臻诗境之最高境界,终于未得,更未知工夫在诗外(工夫在画外)之理之真义究竟何在,以为内涵足恃,殚精竭虑于内涵之经营,虽点画精神,大重表现、感情,然画境本大狭于诗而不得其用,而又失传统文化之精神之本根,此无异于强为巧妇无米而炊之举,尚不足以至写意之境,诚可悲也!论其画者徒以融合中西之路径誉之,尤属皮相之论,足以害人不浅也!由是言之,谈艺者识见必自根本上扭转局面乃可,壮观则审其审美理想,细节则析论其丰富、饱满之异彩之所在,并较诸艺之同异而取长补短,始终之以世俗民生,一以贯之以“我”之至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之历程,否则徒耗才力,无补于事也。
诗之三境,个性、血性、诗性也,后境必兼有前境,诗画相通,往往越血性而得其个性、诗性,故往往不能至“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仅能至“无我之境”,以平和为主,而画境尤擅之也。血性者非一己情意之本性冲动也,相关于人之所以为人、以人为最第一之价值者也,以世俗民生为心而无所回避者也,故吾国歌诗首要之一义为“大”之一字,无是而能成其大者无之也,有之而不鲜明,其所成之“大”亦必具相当之折扣。历代谈艺者每论李、杜优劣,若以此为衡,则杜诗高于李诗非寡一也,杜诗之血性无不相关于世俗民生,其诗境之博大深情、斑斓异彩、驳杂精炼,乃真所谓“大”之境界者矣!近代聂诗卓有灿烂,惜于此犹有所阙也。
诗立于悲剧之上而与之相反,悲剧具丑、恶、怖、畏之因质,而诗则具悲剧性而出之以真、善、美者也。悲剧之最高形式为毁灭也,往往与英雄相关,诗则与悲剧之一切诸酝酿、作用相关,与世俗百姓之寻常生活相关,具悲剧之性质而不可脱除,又缘种种之制约、限制、束缚,而无能致于悲剧之毁灭,但能持续为若干之突破于现实世界,因必历以漫长无休止之煎熬也。悲剧之毁灭,崇高之境界也,英雄之境界也,向上提升之力也,因其毁灭而止;摆脱种种之制约、限制、束缚而臻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持续浸染作为于世俗世界,则豪放之境界,世俗民生之境界,向前而兼有向上提升之力也。人生无论如何总须向前,总须存在,此众生百姓之所常然、必然,故豪放是诗之最高精神境界也。至若豪放之常与崇高纠缠而不可分,则不必言矣。“神味”一义,兼有向前、向上之两种向度,而又能以朴素为之,而能至于烂漫,故诗意者,自根上内在发芽生香之感觉也,余有小诗《长歌》云:“从/根上/发芽//才能/带有泥土的芳香。”即其喻矣。

诗之形式,以细节为其灵魂,表现世间所有之最饱满、丰富、集中、深邃者,惟细节为最能,惟诗为最佳。情景亦细节也,但情景偏重于抒情,远不如事之一义更为细节之本色,而神味更饱满、丰富、集中也。小说亦易以细节为胜,但其意蕴分属整体,且往往不能与作者之主体性情相关,是外人而非自家景色。又西人叙事一体发达,故每重人物性格,如亚里士多德《诗学》论悲剧之六大成分:“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思想”,黑格尔谓性格乃理想艺术表现之真正中心,吾国之金圣叹论《水浒》亦云:“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性格、性情略异,吾国所言性情,乃作进一步讲,盖性格人人皆有,而性情则寓以吾国传统文化所濡染之色彩,而有推崇之意,所谓“性情中人”,大是褒义也。诗以道性情,义在此也。就事论事,则性格无乎不可。性格因情节而见,情节虽为性格而设,却又非全为性格,两者皆重自是无疑,孰为更重,古来论却纷纭。如亚里士多德以情节为悲剧之最要;李渔《闲情偶寄·立主脑》亦谓:“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者传奇之主脑也”,因自作为着眼,故人、事并重,又由戏曲之“传奇”性质,而稍偏重于事也。黑格尔则以性格为理想艺术之最要,金圣叹亦首重性格。原之,无论性格、情节,自作为之角度言之,则情节为最第一,情节创造之难度远过于性格;若自品鉴之角度观之,则人物形象为最要,其中性格为之中心。然此两事,皆易如歌诗中之情景,易陷单调重复,西人近代叙事学大盛,而归纳情节为若干类型,性格亦尔,故金圣叹云:“《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任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相识”,即是矣。且此两者,未甚宜于歌诗之评,未能统文艺而论之也。若深论之,则性格之单调重复更甚,情节可致于深广宽阔之领域,而更为复杂、丰富,较性格为稍胜。情节若到,则性格或随之矣。故避免两者之单调重复,则唯“细节”之一义。“细节”一义不独以最小单位为最大、最丰富、最复杂之形象、情感、意蕴、境界、神味,且能通贯文艺而论之也。“神味”说之“将局部或有限最佳化”,义在兹矣。
诗之最高形式为内在律,其外在形式则仅押韵一事,此诗之“技”之境界之极致,若与论乎“道”之境界,则必与熏染成就于世俗民生之“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相关焉!人之内在有虚实、动静、丰富单调之别,其表现之亦有含蓄、淋漓尽致之分,而若欲发挥内在律至于极致,则非和合诸分别,而主之以实、动、丰富、淋漓尽致不可;而以得自世俗世界之气为本。聚气浩瀚,冲气为激,激而能宕,宕而随我性、自然之变化而为一定之节奏、旋律,无不丰富多彩、姿态万千而完美也。此气得自实际,而形态为虚。唯其实际,故能至于浩然渊闳之境;唯其形态为虚,乃能蓄势待发,以成就最完美之内在律而外见之形式。故内在律之最完美之外见也,则李太白,则关汉卿,则郭沫若,总之为杂言诗也。郭沫若《论诗三札》尝有论云:“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迭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这是我自己在心理学上求得的一种解释,前人已曾道过否不得而知。”实则韩昌黎《答李翊书》早有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又其《送高闲上人序》论“气”之所自:“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可见所谓内在律者,既存于古之杂言诗(其尤佳者则李太白、关汉卿及明季之民歌),而又大见于书中之狂草,他若音乐、舞蹈,皆有此境界无疑也。郭沫若所谓之内在律,与古人只是偶合,故以“前人已曾道过否不得而知”措辞,而吕家乡(见其《内在律——郭沫若对新诗的重要贡献》、《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诸文)则断然以内在律为郭沫若之独创,云其乃由西人“现代情绪”及惠特曼之歌诗之影响而造就,则无异强调此一独创性之同时,而又抹杀其独创性,为西人之附庸矣!而其论诗,则有数误:
一则以内在律为区分新诗、旧体诗之核心要素,为郭所创之“新的韵律体系”,而内在律非新诗所独有者已如上述,其误甚可易知;且以此为据,仅自形式一因论新、旧诗之异,形式固为歌诗演进之重要因素,然却非根本因素,此论颇如论词、曲之非律诗,莫能得其要也。而不知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有“诗、词、曲,皆诗也”之论(沫若词论亦非新见,宋人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谓词“根情性而作者,初不异诗”,元人王若虚《滹南诗话》中亦云“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故诗之形式纵有变化,其诗之所以为诗之本根却一也。又云“韵律是诗的生命,没有韵律就没有诗”,此提升韵律至于诗之本质地位者,无之则非诗,据韩昌黎文可知,韵律亦为文之要素,非诗所独,如其《祭十二郎文》,声情并茂,气味充沛,乃内在律实现之杰作,由此亦可知内在律之为韵律非诗之本质、核心、本根所在;且其又云“诗,不论古今中外的诗,都必须具有韵律美”,则逻辑亦与前论相悖:诗既皆有韵律,则所区别者盖为佳与否耳,则适与“韵律是诗的生命”为矛盾也。
一则以情绪为内在律之核心要素,而不知情与气之合一乃内在律之核心;且气为其本根所在,如上引韩昌黎《送高闲上人序》文可知。引郭沫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之论为据,实则郭沫若此论亦非创见,英之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有云:“我曾经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有一种反映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一篇成功的诗作都一般都从这种情形开始,而且在相似的情形下向前展开。”(曹葆华译)故中心意旨乃在情感之密度、浓度、力度、深度、强度、色度,而此皆来自于“气”之一根本因素,气若不能浩然沛然为盛大之态,则如华兹华斯者虽具“强烈情感”,却仅堪为浪漫主义诗人之以消极为色者也。如浪漫主义诗人之积极如雪莱、拜伦者,则皆重激情、想象,郭沫若虽未论此,却能于歌诗中气、情兼俱,为豪放壮丽之境界,此以其自身之气质内养使之然,论纵能至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之境界,而辨郭沫若之独创,亦不当仅面向古人,而以拾西人之唾余为事也!故郭之于内在律,足以当继承而发扬光大之之誉,却非独创也。又吕氏虽论内在律,而实偏重于抒情诗也,吕氏引郭沫若语“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以论“情绪的直写”,可谓善偷换概念而以偏概全,若如此者,不知置叙事诗于何地?而吾国歌诗史乃乏叙事诗之历史也,元之剧曲之所以突破意境理论全在叙事之一因素,若仅以情绪之直写为其最佳之所在,则不可也。
诗之外在形式之加强,仅能精炼诗性、诗意,而不能自根本上提高之。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语,虽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而较生动,然此语之诗意已基本奠定,境界之生动与否,无关于其境界、神味之提高也。又如陶渊明《和郭主簿》之“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贮”字何其精彩,然炼字虽将其中之意蕴提高至最丰富、最精彩,而终无与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