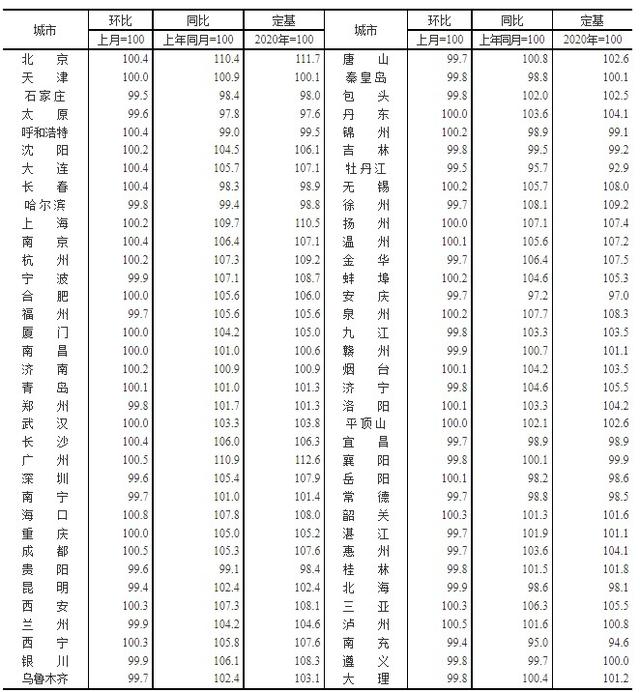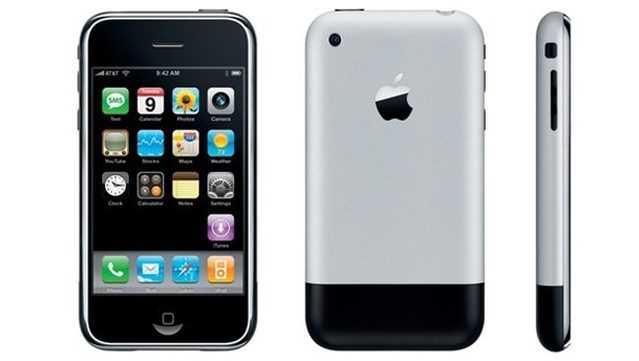阿特休尔说:“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4]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和来自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封锁,国家需要新闻媒介动员和鼓舞民众,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发展、社会建设服务。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认同“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也使得报纸的政治职能强化,更多地承担了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功能。“1949年后官方依据阶级斗争政治理念,贯彻根据地时期建立起来的党报模式,按照人为设计出来的‘外部规则’建立一种新的报业秩序”[5],而《大公报》只能努力融入这种新的报业秩序中才能继续生存发展。
融入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面对新的话语方式、新的盈利模式、新的报刊分发渠道,大公报人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在强化了报纸的指导性后,私营报纸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超党派’立场的新闻没有了,‘内幕新闻’没有了,‘本报专电’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没有了。”[6]就新闻信源而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国家对舆论的态度由放到管。以1950年8月15日的《大公报》上海版为例,当天《大公报》的头版刊登的几乎是来自新华社的专电,如“朝鲜解放五周年纪念,毛主席电金枓奉致贺,周恩来总理电金日成首相”、“朝东海岸要港浦项解放,洛东江东岸美敌图顽抗受挫,美帝隐瞒伤亡人数引起内部攻击”、“在安理会会议上,马立克严斥美英代表,指出朝鲜情势为中国情势重演,美国及其附庸阻挠僵局的打开”等等。新闻信源的单一化使得《大公报》失去了其素来在新闻信息丰富多元方面的优势。
(二)经济因素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创办的《大公报》作为一份经济完全独立的民营报纸,发行和广告是其主要经济来源,而“建国初期严格的新闻内容管制和随后实行的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在发行市场上面临一种不利的局面:办报特色逐渐淡化,新闻报道无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即读者对私营报纸的需求量下降;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的读者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要求私营报纸本地化的措施,使原来具有全国影响的私营大报只能放弃外地市场,条块分割扭曲了报业的发行市场”。[7]同时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这也导致《大公报》的发行量逐步减少。以上海《大公报》为例,解放初期其销量为16万份,“后逐年减少,1952年下降到6.3万份,广告收入大减,仅为4年前的40 %。到1952年10月,报馆合共赔偿41.5837多亿元,折合美元大约20万元,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8]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过程中,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方针,“1950年3月,全国有私营报纸58家,同年下半年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实行公私合营,1951年8月私营报纸减少到25家,到1953年初,全部实行公私合营”[9]。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党和国家“正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客观形势要求有一张以财经为重点的全国性大报”,以对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进行及时的报道,而《大公报》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具有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人才和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有能力承担起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宣传报道的责任。加之其在经营上遇到了经济困难,党和国家决定将大公报天津版和上海版进行合并,迁至北京,专门进行国际新闻和财经金融政策的报道。
(三)社会环境

对民间报纸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体现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两大群体之间的博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精英以报刊为主阵地,对国家未来前途做了一系列伟大畅想,而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开始由对知识精英的崇拜逐渐转向对政治精英的崇拜,社会话语权也由知识精英向政治精英交接。所谓的政治精英,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一般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掌握权力或处于首领地位的人。政治精英是一个社会的领导群体或阶层,其兴起的同时必然对知识精英产生了或有意或无意的压制,有学者认为,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成为一种新传统,在政治精英领导下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普遍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营报纸在建国后遭受冷遇。《大公报》在新闻采访方面表现卓越,新闻、通讯颇具时效而有血有肉,因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然而,建国后《大公报》在新闻素材的收集上遇到了制度性的阻碍,同时常常因为民营报纸的性质而受到被采访单位的歧视、冷遇甚至拒绝,这在客观上对《大公报》自身的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其逐渐转型成为党报体系中的一份子、人民群众新闻事业中的一员。
四、结语
报刊业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报刊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命运走向,我们能够获得的认知是:在党报占据绝对核心地位的时代,民营报纸发展艰难,纵然国家为民营报纸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但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大多数民营报纸难以真正适应并融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最终走向了停刊的命运终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当下,媒体如何平衡政治和经济两股力量,真正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更好地实现其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每一个媒体人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和积极实践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前言.
[2] 肜新春.时代变迁与媒体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59.
[3] 肜新春.时代变迁与媒体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73.
[4](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37.
[5] 江卫东.建国初期《大公报》新闻报道困境考察——以规则博弈为视角[J].学术交流,2015(12):203-208.
[6]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61.
[7] 施喆.建国初期私营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J].新闻大学,2002(1):54-58.
[8] 新记大公报史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410.
[9]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