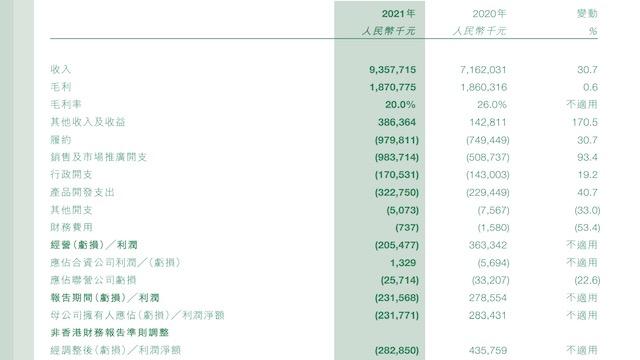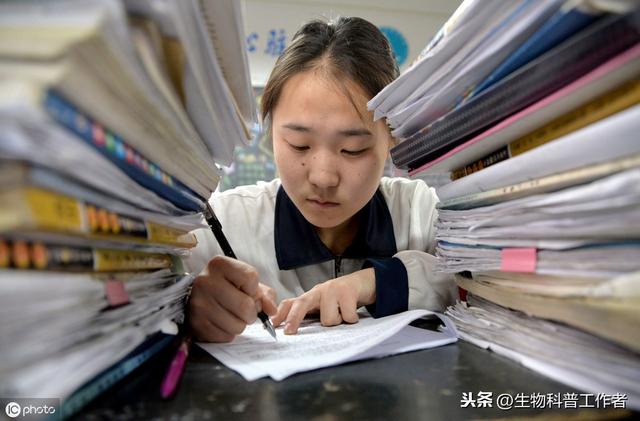线条是书法的最小单位,其次是结。
单个单词本身的结构,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已经成为一种规则。书法家不能改变它的基本形式,更不能创造它。书法家能做的就是“结”,所谓“结随时变”。“扎堆”是通过不同的“布与白”使用相同的文字和符号的生动造型,各有不同,但符合时代审美。
随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布白字越来越多,布白意识也日益解放,从空白制服的方形中挣脱出来,草书的出现,强化了空之前的白字意识。
为什么同一个字可以写出无数种风格,创造出许多风格各异的书法家?因为我们有相对的自由去分空白。如果空白的大小和形状都像笔画结构一样严格,书法艺术就无从谈起。正因为书法是和文字捆绑在一起的,在空的一定时期内,它可以让我们随意的变化,随意的划分,让书法不断的传承,发展,变化。由于不同书法家的书写习惯不同,笔画长短粗细不同,点画与点画的距离不同,导致结构布局中密度、大小等各种复杂的变化,形成了一些书法家字的结体方式。
古人云:“书是用墨写的,书的美是不用墨写的。只有迹象,但无处是魅力。”书法家要想取得艺术成就,不能停留在浅显易懂的阶段,像某一派,可读不可读,而必须不断开动脑筋,在布白上做文章。
所谓白,简单来说就是指白色宣纸上没有笔画的地方。这些空白被当作“布白”,清代蒋鹤巴空白的分类如下:“布白有三种,即字里、字里、字里行间的布白。
其中“一字中白布”指的是“结”,即一字内部的空白色分布。
古代书法家说布白,而不是“布黑”,意思是书写时注重墨色形成的线条,不能忽略白空白的地方。
要注意安排字符的空间隙,与黑字形成对比和关联。
有些高明的书法家讲究空留白,使得整幅作品中的空留白井然有序。良好的空意识是优秀书法家的重要标志。
但是,普通书法爱好者在练字时,总是盯着字帖上的点画,一笔一笔地练,只注重字的点画和线型,以此来学习书法艺术,导致写出来的字缺乏韵味和美感。这样理解“写作”,空白色的惯性会固化,艺术会越来越降低它的艺术魅力。
主要原因是审美习惯的固定化倾向。笔一接触纸张就形成点画线条的运动,使我们的视觉不自然地停留在点画形式上。对单词本身的结构形成固定的观察模式。
知道了这些道理,发帖时不仅要时刻注意线条和墨迹,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被黑白隔开的空处、无处和白处,也就是没有墨迹的地方& # 34;怀特& # 34;觉醒和空精神。发帖要盯着点画室空白练,才能进入高境界。
单字结内空白的形状是由点画的位置决定的。一般来说,结内越规则空白色,运动感越弱,造型越稳定。反而产生动能和形能。就楷书而言,布白排架结构有几种排列方式,如叠置、避让、顶穿、穿插、面向后、侧靠、补充空、覆盖、承接、粘合、借用、替换密度、大小等。草书很复杂,包括各种空白。
各种书法风格都会根据字的点画形式和数量以及部首的不同组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适当的排列。古帖排白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布白统一。
这也是古代书法家孙所说的,初学分配,但求公平正义。也就是说,笔画在规则下大致均匀分布,笔画以外的那些空白,大致相等,看起来匀称。如果一个字有多幅横画,一般按照平行等距的原则处理,这是布白统一的要求。满足布白均匀的要求。
二是通过断开、交叉、组合,在纸面上形成空白色的不同形状。
这样的空白色的是比较规则的图形,或者圆形,或者四边形,或者三角形,等等。如怀素《自叙帖》中的空白色形状中有许多闭合的形状空,呈相对规则的圆形、椭圆形或弧形,成为《自叙帖》空之间造型的主要方法。
二是空白极其危险,就是不规则空白,追求不对称。传空白形成危险。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布保主要是通过线条的长短粗细、结构变形等的重组,主动有意识的创造出来的。,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力的动态空白,与字外/[k0/]白或行间空白相连。比如张旭的《古诗四首》中,绳结内部的空白色人影或被压缩或被夸张,或原本开阔的空白色人影被改造成更大的封闭空房间,或反过来形成强烈的对比,激活空之间的人影。再如黄庭坚的《李白怀古诗》,用断开的“点”使线条断断续续地出现粗细,创造出不规则的布白,有的甚至收缩到无空白,成为局部的块墨。朱运明的结体空白形也善用“点”来塑造空白,甚至是由点组成的单字的形状,使结体空白与行间空白没有区别。
第三,密度变化形成的布白。

除了从字体的角度划分,单个字的内部布局也可以从黑白的分布区域看出。就是用密度的对比来布白。
论词的内部密度。苏东坡曾说:“大字难密,小字常局促”,大字难密无痕,小字难宽敞有余。
王羲之善于用疏密来安排留白。他大胆运用省略、组合等密度对比的手段,加强文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为什么很多人学王羲之学得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密度引起的空白度不被重视。大多数人把王羲之的字帖上的黑块分开,由笔画组成,几乎融合成一团。这虽然有助于辨认笔迹,但却失去了王笔下人物“密不透风”的神韵,密度对比强烈的俊朗之气荡然无存。苏东坡学王学得透彻,敢于大规模用墨,形成墨棒效应。
孙的《诗经》大部分词的空之间的布局很有讲究,总有一个大空的空位,让人觉得是那么的有新意。
结构中密度的关系要大胆处理,有的点画排列要松一些,有的点画排列要密一些,不能让密集的间隔增长,点画排列之间要留有粗体空的留白,做到密度协调,气势紧空精神。使之不要太稀疏,不要太密集,字的结不一般化,不落入寻常俗套。总之,可以密密麻麻,巧妙组合,同时产生新意,给人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结子时要刻意做出的空白色,能给人空精神、呼吸顺畅、想象空空间的美感,从而给人独特的审美快感。当然,密度的安排要建立在自然表达的基础上,而不是有意或人为的。
一般该疏的疏,该密的密,正常的疏密结合比较好处理。至于疏与反密,密与反密,密与密结合,适当变化,也不容易。作者必须有很高的意境和技巧,否则很难做到。
从使用效果来看,单字密度趋于稀疏,空之间留白较多;字的内部密度倾向于“密”的一边,空之间留白较少。
第四,布白的简单与复杂
为了让画面空白更有审美意义,既“简单”又“复杂”。白布的形式单一会“单调”、“贫乏”,形式过多会“繁琐”、“累赘”。
“简约”并不排斥对重要部分的深入细致的表现。“复杂”并不是说画面中要有尽可能多的白色东西,也不是说文笔不要简洁扼要。“复杂”是写作中对重要部分的精辟描述,也不排斥对无关紧要的部分进行删节。要在黑白中寻找图案,通过对黑白的理解和巧妙运用,在“简约”中表现多彩的世界,创造特殊的艺术效果。
“简单”和“复杂”的布白技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一般来说,简单型更简洁、概括;复杂的形式更具体、更丰富。对于真正想创新的艺术家来说,这两种方法都值得关注,要适当穿插。
五、大、小布白
空白色要合适,空白色太松太弱,空白色太紧太局促。空处理要有“度”,没有标准,只能根据人的综合感受。比如“大空白”给人一种沉稳安静的感觉。如果空白色太大,会让人感觉空孤独。
空字帖中的白色能给读者新鲜感。“空白”越大,联想就越丰富。意义的不确定性。回味和遐想效果的起点。
比如我们常说大家都生气,为什么会大?空白色零碎,则显得胸襟狭窄,斤斤计较,而空白色过于分割,笔墨过于细腻,不显慷慨。只有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它们的重量比,也就是把握好规律的度,才能把黑白的最佳效果展现出来。
5.单个单词中的空白也应该是有意义的形式。从空白中求韵,从空白中求意境,在书法意境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
学习单词的版式时,不能只看单词,要结合规则来看。为了作文的需要,结字的布局也要相应变化,有的紧,有的疏,有的舒展,有的紧。
纵观书法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布白,并且空白的量有增加的趋势。后世书法越多,大块空白越多。
6.临摹时我们如何观察和学习空白布局?
读书时要突出布白对称,草书其实是有错有改的。包括同体同字学不同布白。空白变是由关键学习结的收放变化引起的;点画粗细的变化,抬压的变化,对单个字的布局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注意布料和白色的对比。张贴的准确性不仅取决于张贴内容上圆点的形状,还取决于对比度空白色。一对比就知道哪个松哪个紧了!布白对比是练字很重要的捷径!
临摹时注意对空白的比较理解,有助于提高我们在书法创作中的想象力和对空白空的利用和掌握。
光靠临摹学习是不够的。你也可以不断地发现和学习世界上所有千变万化的事物,比如绘画、雕塑、建筑等。在书法中,你可以欣赏和利用黑白空之间的分割和交融。
书法是分空白的艺术,但分空白不是写书的目的,书法作品的标准也绝不是空白或墨。最终的标准应该是,意境书法家不仅要有关于对称的规则,还要有灵活性,不求摆脱或束缚于规律。
在审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原则下,通过空白的艺术处理,一个字的笔画、结字也能达到一种变化多端的美感和多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