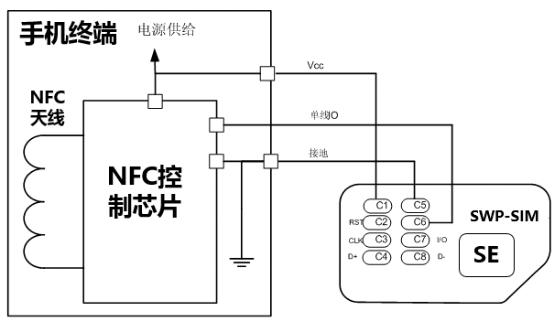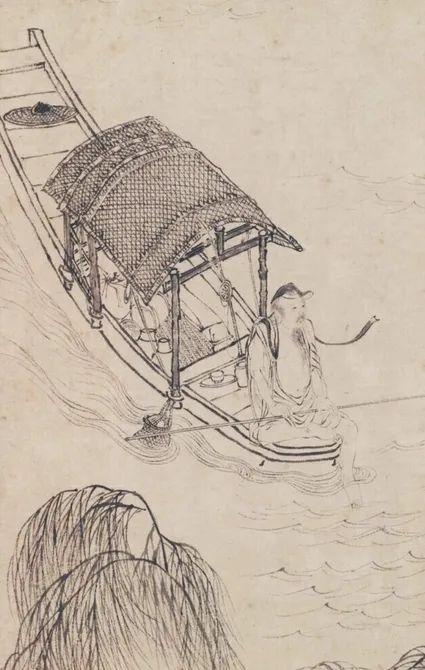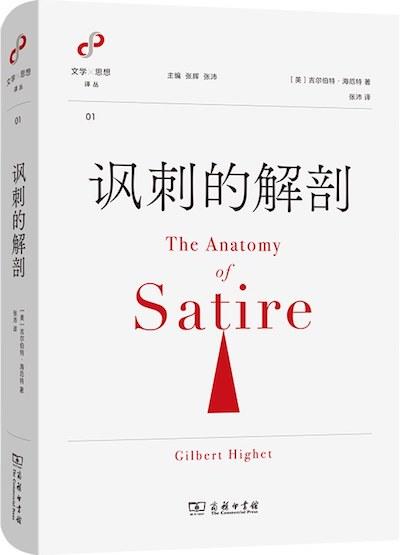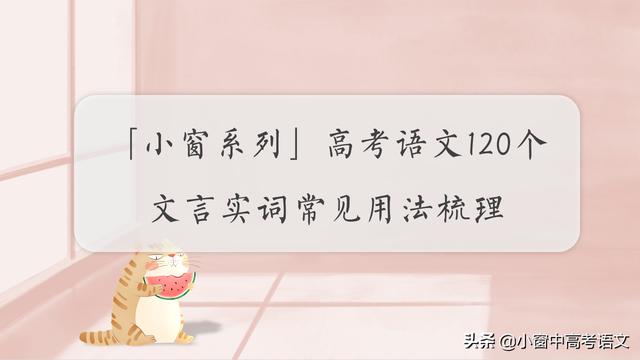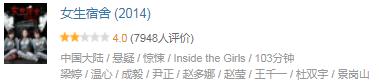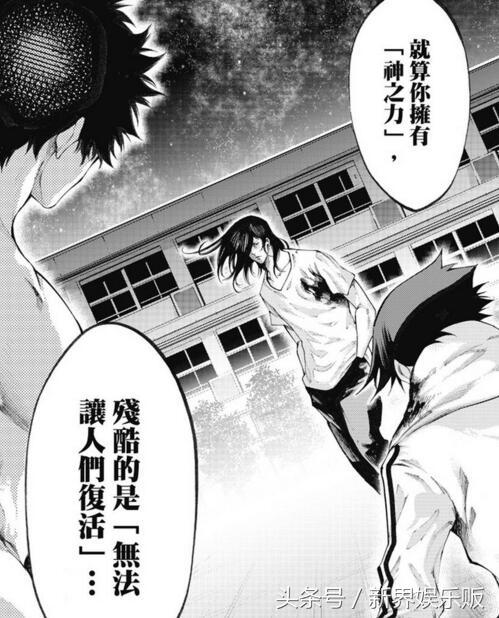相磊
近年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常规的社会问题。自2016年、2017年谷歌围棋机器人AlphaGo与李世石、柯洁两位世界级棋手对决以来,人工智能仿佛走出了技术的高级法庭,成为人们构想技术革命下人类未来生活的最重要标志。如今技术层面的开发与实践,奇点临近的前景与讨论,关于有一天会有多少工作被AI取代的争论与假设,SIRI不过是个闹钟机的戏谑感觉,以及无数综艺节目中刻意唤起的“渺小”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画面。这张图的背后,是一种普遍的心态:人工智能必然会戏剧性地影响人类的生活,但这种改变似乎不会发生在目前看似迫在眉睫的任何一天,所以态度的延迟和流动是允许的,人们需要在一个又一个随机的讨论中逐渐找到与人工智能相处的舒适节奏——与同样焦虑下的人在一起。
于是,围绕着很多物体,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对话不断上演。其中,文学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最具象征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微软的《萧冰》和清华的《九歌》,其诗词往往在隐瞒创作者真实身份后“假作真”,被认为是真人所作,甚至还有发表过的诗词。在各大视频平台上,很多以“AI续作”为主题的直播录制和系统开始涌现。要改写的对象不仅有《蝙蝠侠》、《审判反转》、《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知名的大众文化作品,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桃花源记》、《两个孩子的争论》等。,或是已经进入经典序列的文学名著,或是基础教育教材中的传世佳作。各种人工智能逻辑连贯但画风清晰的“神展开”,自然充满了节目效果,甚至培养了一批热衷于观看此类视频的永久观众。在网络文学领域,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蔡赟孟晓等AI写作软件的推出,使许多有特定表达或阅读欲望,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得到满足的潜在作者和读者,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完成这些关于文学的尝试和愿望。
与这些现象同时发生的,是人们对艾文学活动的各种价值判断: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作品低劣粗糙,算法作用下的机械排列组合冒犯了文艺的高尚内涵;有人认可人工智能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相应的工具价值,但它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萧冰》的欣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诗歌模糊多义的特点和读者的过度包容,艾实力远非逾越人类权威。也有一些人没有给人工智能下定义。他们大多是来自“互联网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他们对话语场的辩论缺乏兴趣,但对AI写作的趣味性和张力非常在意。
让AI输出文本的本质是用计算机语言模拟人类的自然语言,属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范畴,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部分。对于人类来说,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作为一种智能表达,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言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神圣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能力。除此之外,还有类似的定位,比如会使用工具,会艺术创作等。——文学语言恰好处于发明语言和创造艺术的交界处,尽管这一观点后来被人类学的一系列实验证伪,但它仍然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常识体系中:在大众中,它扮演着人性的重要角色。
在智力危机成为与科技无关的普通人每天热议的话题之前,人类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质疑和思考,为什么自己是人而不是其他生物,尤其是近代以来。机械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紧迫感。机器对人类诸多智能的追求,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问自己:人类的特殊性是什么,什么是机器做不到而只有我能做到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多答案,比如自由意志,比如合作和共情,比如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答案本身可能会随着人们对世界和自身认知的推进而慢慢过时,但人们总是需要相信,一定有某种像坚硬的、无缝的、无懈可击的内核一样闪闪发光的东西深入人心,这就是数理逻辑永远无法模仿和理解人的原因。这种信念有许多具体的体现,其中文学精神是最重要的一种。
在这个前提下,那些对艾文学写作行为的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立场:维护人性的高尚;认为AI没有威胁,比不上人类主体;并且热衷于在AI和自己之间建立一种想象的联系。三者中,前两种思路更有力。其实它们由来已久,直到人工智能写作现象引起广泛讨论,它们才发生在文学领域。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回到此刻,把写人工智能的题材换成网络文学,会发现一切都是同等匹配的。质量差,品味差,有损文学精神,但通俗只能使初读难以高雅。艾在尝试创作文学时得到的评论,与网络文学诞生20多年来经历过无数次的评论如出一辙。这是巧合吗?或者说,两者背后,隐藏着哪些关键的相似之处,引发了主流舆论如此相似的反馈?
他们的数字基因是目前最有可能的正确答案。网络文学自不必说,作为在网络空间空产生和流通的文学形式,是其基本属性。此外,网络文学所写的故事,与当下人们生活中的媒介体验密切相关。如果说AI写作是用机器语言模拟文学语言,那么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就是在用自然语言再现一种基于计算机语言和自然语言的生活体验。是的,虽然SIRI就像一个闹钟机,即使“小杜”只负责回答电视节目中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在更多突然察觉不到的细节中,在人们深陷其中、实际度过的每一天里,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早已开始交融——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又有多少其他事物没有屏幕中介的影子?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媒介变革,人们长久以来建立的知识、信仰和价值体系还没有做出连贯的反应,而写人工智能、网络文学等实验和趋势,则在暗示着人性变化的更深层次的表现和表征。他们因数字化基因而遭遇的排斥反应,或许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个虚实和谐、人机协同进化的时代,文学精神应该被重新审视和定义。现代的人文主义观念是否过多地建立在由古腾堡的创作、叙事和平面媒体构成的文本模式上,以至于在新的数字时代到来的时候,已经无法应对此刻人们潜在的新的精神浪潮。在捍卫文学的神圣和人的本质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捍卫自己所想的吗?在这个辩护的过程中,有没有更微妙的被忽略的可能性?
第三种心态的持有者正显示出这种微妙的可能性。在《AI延续》视频的评论区,在网络文学的线上社区里,也有这样更开放态度的人。他们不仅能毫无阻碍、毫无负担地在AI的蛮横操作中找到类人影子,还开玩笑地称赞其“像奥亨利”、“雨果奖”。他们也可以无视人类所谓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沉迷于效仿艾的文学来制造“去伪存真”的效果,像游戏一样给人们引以为豪的文学精神添加人工智能。他们不拘泥于古典、文学性等已有的观念,更在乎世界观设定是否宏大壮阔,人物设定是否足够吸引人等等。对他们来说,人工智能和网络文学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异质性。他们并没有暗中计划取代人类或者总想亵渎文学,而只是日常世界的一部分。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以兼具数字逻辑和人文精神的心态,从容地沉浸在数字创作、阅读和互动中,逃离纸媒时代作为文学的为人和文学的束缚,接受并开启文学精神的新维度。

当然,回到现在,写人工智能还是幼稚的,《AI续写》系列视频的观众通常是被其蹒跚学步的稚嫩状态所吸引,“蛮横”、“哈哈哈哈”才是即时弹幕的主流。在网络文学领域内,用AI辅助写作还是一件不方便的事情。很多作者和读者还在讨论文学性和原创性的概念,媒体的视野急需引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来到一个相当特殊的时刻,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象每一种现象、每一种噪音背后更高的未来。自然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正如文学也是人之所以为文学的原因,但它们可能不是固定的,等待人们去追寻或守护的奥秘,而是流动的精神,在世界上是新的,永远是新的。
编辑:诸樊
校对: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