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江苏省调查组发布了“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通报。但是,该通报让公众产生了新的疑问,因为它依然是以受害者杨某侠的婚姻有效为基础进行的,虽然通报中已明确指出民政部门在办理婚姻登记时存在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没有触及对杨某侠婚姻相关法律问题的处理。笔者认为,关于受害者婚姻效力的质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具体到处理程序上就折射出了我国目前法律在婚姻效力认定上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亟待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内的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在修改或立法时予以修正或解决。

婚姻效力认定程序的提起主体
《民法典》将婚姻的效力区分为无效与可撤销。关于无效婚姻,法典第10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可以看出,该条款只是提供了判断无效的实质性标准,至于如何确认无效,并没有触及。对此,不乏有观点主张婚姻无效应为当然无效,无须确认,但是实践中终究是存在着大量有关婚姻效力的争议。因此,法律上必须设置相应的程序对婚姻效力予以确认。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9条第1款规定,“对于第1051条三种情形请求确认无效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予以确认”。这一条款明确了基于第1051条规定无效的情形只能由法院进行确认,提起确认之诉的主体包括当事人和近亲属。关于近亲属的范围,则除重婚事由可由基层组织提起之外,其他均为近亲属。
关于可撤销婚姻,法典第1052条第1款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就何为“胁迫”,《〈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18条第1款规定,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由此可见,提起撤销婚姻的主体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

综上,从现行法来看,无论是无效婚姻抑或可撤销婚姻,在认定程序上采用的都是民事诉讼形式。而且,法定提起主体的范围相对狭窄,主要限于当事人本人。在无效婚姻上虽然主体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是扩大到近亲属或基层组织。这种限制虽然与婚姻自由原则有关,但也与我国社会中认为婚姻属于“私事”的法意识有关。正是受这种意识影响,国家对婚姻效力秉持着一种不主动介入的态度。
婚姻效力认定权限的过渡与交错
我国法环境下婚姻效力的认定权限一开始并非由法院享有,而是由婚姻登记机关行使。只是随着民法的私法基本法地位逐步确立,这一权力才逐渐过渡给法院。关于无效婚姻,1986年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第2款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当宣布该婚姻无效”。由于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随后的司法解释将婚姻无效的宣告权配置给了法院。2003年制定的《婚姻登记条例》随之删除了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职权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这种做法在《民法典》中得以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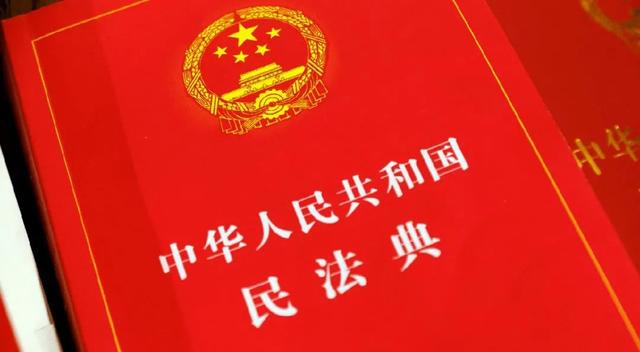
关于胁迫婚姻,2001年《婚姻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可见,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均享有撤销权力。当然,无论哪一种撤销,均须依据受胁迫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之后,《民法典》将这项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法院,规定当事人只能向法院请求撤销。
但是,因婚姻登记程序本身瑕疵导致婚姻登记被撤销,进而引发的婚姻无效如何处理却成了法律遗留的问题。对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17条规定,“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也是沿袭了2001年制定的《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一)》的规定。
也就是说,1986年《婚姻登记办法》中婚姻登记机关可依职权撤销婚姻登记的做法在现行法中已经没有任何踪迹。加之在将婚姻登记行为视为行政行为时,行政行为具有的确定力又要求相应行为的自我纠错必须有法定的依据和理由,对于婚姻登记的撤销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形式进行,且提起的主体只限于当事人。由此,实质上就导致了婚姻登记机关自我纠错的不能。

或许有观点认为,根据2021年两高、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民政部门可以直接撤销相关婚姻登记。但是,这一规定只是指导意见,能否创设行政权限,非常值得推敲,这可能也是江苏省调查组没有适用的原因。
婚姻效力认定制度的修正
我国在婚姻效力上采用的是完全由法院主导的结构。这种结构在现实中遭遇到类似“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这种被拐女性的婚姻时,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虽然婚姻登记程序存在着严重瑕疵,或者虽然存在着《民法典》规定的无效或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但是因为被拐女性已经处于精神障碍状态,效力认定提起主体又存在严格限定,司法权的消极性就会导致公权力无所作为的问题发生。对此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扩大各类效力认定程序提起主体的范围。
尤其是在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中,提起的主体不应再限于本人或近亲属,而应允许检察机关也能够提起诉讼。因为,婚姻不宜理解为纯粹的“私事”,它不仅会涉及子女等第三方的利益,也会像被拐卖女性婚姻这样引发社会普遍担心和忧虑,这些都应被纳入公益的范畴,构成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根据。而且,从比较法来看,已经有诸多先行做法。例如《日本民法》第744条规定,“违反本法第731条至736条规定的婚姻,可由当事人、近亲属或检察官向法院请求撤销”。这点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修订时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法理上重新定位婚姻登记机关的性质。
关于婚姻登记机关,性质上不宜再定位于行政机关,它所行使的权力也不宜归属于行政权。定位于行政机关的观点由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力对社会全面管治的秩序中脱胎而来,它也是实践中导致诸多不必要的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双轨制”复杂交错局面的根源。在民事活动中,登记只是婚姻行为有效的要件之一,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只是公权力机关提供的具有公示效力的证明而已,完全无涉行政权行使。依此,对于登记程序瑕疵的救济也无须再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由法院在书面审理基础之上直接裁决即可。
最后,国家监护制度的完善。
在被拐女性存在精神障碍时,还涉及国家监护问题。尤其是就被拐女性婚姻被认定无效或撤销之后,如果缺乏监护人或监护人不能正常履行监护职责时,就需由民政部门依据《民法典》承担起监护人的职责。民政部门此时的监护职责不能被理解为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是个人在遭受工伤、职业病、疾病或自然灾害时由民政部门代表国家提供的各种补助;而国家监护却是针对精神障碍患者这种行为能力存在缺陷或不足提供的特殊保护,权限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在婚姻上的各种权利,故应当注意区别。
(原文刊登于《上海法治报》3月2日B6版“法治论苑”。责任编辑 徐慧,见习编辑 朱非)
作者 | 郝振江(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