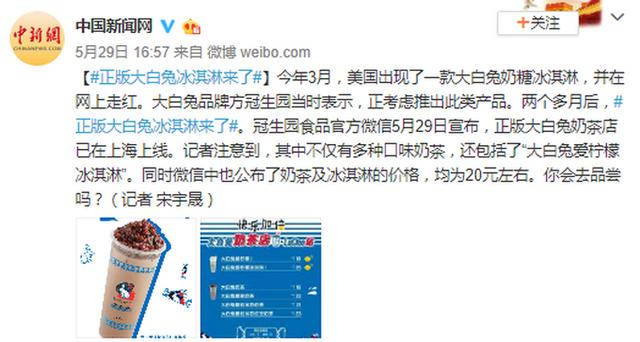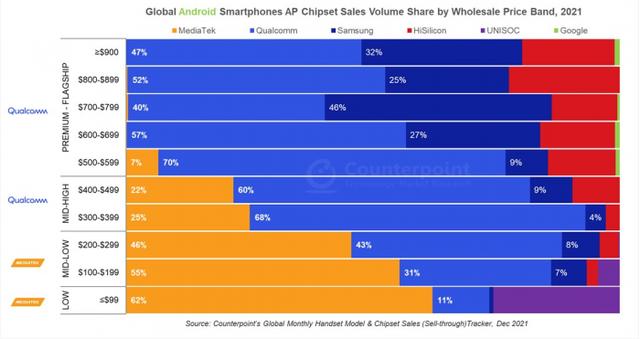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儿问我:“你说《老师•好》是悲剧还是喜剧?”
我脱口而出:“悲剧啊。”
女儿却说:“那为什么别人都说是喜剧片呢?”
我有点诧异。是啊,为什么人们都把《老师•好》说成是喜剧了呢?难不成媒体及观众都因于谦是个相声演员而忽略了文学常识?于是我觉得有科普之必要。
关于喜剧和悲剧的定义,鲁迅的一段话是权威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一般文学理论的书籍把戏曲分为三类,喜剧、悲剧和悲喜剧(正剧)。其特点分别是,正剧的风格是偏严肃沉郁的,而喜剧的风格是轻松搞笑的。正剧也被称之为“严肃的喜剧”。悲剧的结局是悲惨、缺憾的;喜剧的结局是圆满的,即所谓“皆大欢喜”。而正剧的结局一般是问题得到解决或者部分解决。
具体到《老师•好》这部影片,其结尾显然既不够“悲惨”也没有“皆大欢喜”(毕业照苗老师缺席,安静的“被命运抛弃”)。
我之所以说这部影片好,根本的原因就是它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则是它完全基于现实生活的基础、细腻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及人物情感的真实。我认为“真实”才是文艺评价的基础。而美学意义的批评则主要看其与观众的“共鸣”即所谓“走心”程度。当然,如果从纯艺术技巧的角度批评,这部影片又是有着明显缺陷的。硬伤就是完全没有交待的“师母的消失”。师母是个觉悟不高的家庭主妇。在电影前半部分塑造得很真实、得体。而在“苗老师怕耽误安静学习,他把学生接到自己家里补习,还告诉大家不收费。厨房的师母听到后,刻意加重剁菜的声音表达不满”。这个细节之后,师母就完全消失再没出现了。而观众对于苗老师的关注程度似乎抵消了对这个硬伤的注意。

如果要从“人物标签”的教条上看,似乎也可以“否定”这部电影。比如苗老师这个“地区级”的优秀教师,上课第一天就做出没收口红、小人书等等开始“丧心病狂”的行为。他“自大独断、唯成绩论,自己的自行车被拆,第一反应就是把罪名按到成绩最差的男孩头上。扼杀学生可能性,也没忘了洗白自己——我这都是为你好” 等等也可以饱受诟病。但这种“批评”已经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了,而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标签似批评——用教条主义的态度,脱离现实背景及人物情感的按“好人还是坏人”的标签进行批评。
上面所提细节实际上正是对“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师生关系最真实的写照”,是为了“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从而引起人们对“教育如何深化变革才能建立起融洽、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的深层次的思考。
而电影刻意把安静的致残与苗老师“一切为了学生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人性大善”作比较来结尾,实际上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颇具悲剧色彩的。但这个悲剧是“不动声色”的、委婉的。如果我说是悲剧而不容易被接受的话,理解为“悲喜剧”是比较合适的。

撰稿:颂明

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相关链接】